內容簡介
《源創新》是史丹福大學教授、企業創新轉型策劃大師謝德蓀(Edison Tse) 的關於中國企業創新和中國經濟轉型的理論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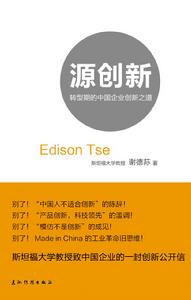
作者謝德蓀專業理論深厚,曾親身經歷矽谷創業,自2003年以來,他在中國講學、考察發覺中國企業正面臨著尷尬處境,於是潛心收集案例,做了大量的研究。最終,由對國內外案例的海量分析,找到了適用於轉型期中國企業的,切中時弊的破解之道——“源創新”。
源創新”即從源頭上創新,相對於科技創新、產品創新、流程創新等常見概念,它代表的是一種極具顛覆性的新思維。它針對波特價值鏈理論的局限性做出突圍,從根源上糾正了工業革命舊思維,提倡以“源創新”建立適應於資訊時代的“兩面市場”生態系統,實現從以“產品”為中心到以“客戶”為中心的轉變,為多方客戶提供新價值。
這是一場思維革新的鏇風,在書籍的腰封處,響亮的四句話痛快淋漓直指中國企業時弊——
“別了!‘中國人不適合創新’的陳辭!”
“別了!“產品創新、科技領先”的濫調!”
“別了!“模仿不是創新”的成見!”
“別了!Made in China的工業革命舊思維!”
作者簡介
謝德蓀(Edison Tse)是坦福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系教授,亞太中心主任,“創新戰略理論和創新商業模式引發新市場”研究領域的最前沿學者。謝教授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工程博士,因所在領域的傑出成就,被授予美國控制協會Donald Eckman大獎,並曾任國際一流學術雜誌《IEEE學報》副主編。
多年以來,謝德蓀教授一直致力於高科技產業創新與發展、經濟系統模型、戰略與競爭分析、中國創新及轉型的研究,在國際權威雜誌發表論文180多篇,逐步發展成為以創新戰略生態系統、兩面市場體系為核心的源創新理論。該理論為中美各類型企業及政府決策部門,在結構調整方面找到了突破口和富有實效的轉型路線,獲得政商界著名領袖們的高度讚譽。
謝德蓀教授擅長把研究活動和實際套用相結合,參與創辦了著名的人工智慧公司“企業決策系統(ADS)”及verity公司(NASDAQ上市企業),因此受邀擔任美國多家大公司和政府機構技術和商業諮詢顧問。近年來,更是被中國廣東移動、首都機場集團、首創集團、長影集團、國信集團等多家中國大型企業聘為顧問,幫助中國企業規劃和制定商業生態系統和動態戰略,以及成長擴張的創新金融戰略。
自2004年以來,謝德蓀教授作為斯坦福專業發展中心(SCPD)的首席專家在中國各地講學,先後與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國家外國專家局、中國衛生部等國家機構,香港、江蘇、湖北、浙江等地方政府和機構合作,推出“中國企業新領袖培養計畫”、“政策分析證書課程”、“中國地方及企業轉型課程”、“香港金融工程”等培訓項目,其源創新理論深刻地影響了轉型期間中國企業的發展,並有效地幫助地方政府實施區域創新可持續發展戰略。
序言
中國人如何創新
牛文文
中國人到底會不會創新、能不能創新?這在今天好像成了一個世界難題,或者說世界疑問。五六年前,《世界是平的》一書作者弗里德曼訪問中國,在午餐會上曾經向我們幾個財經媒體人提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企業創新的因素到底有多大“比例”?有沒有5%?當時在座的都無言以對。這件事後來被大家總結為“弗里德曼拷問”——到底中國的企業有沒有創新,會不會創新?中國人在商業上的創新力如何才能提升?有一種普遍的認識:中國經濟30年的成功,主要還是建立在引進、複製、大規模製造上,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和引進外資的結合上;這些年中國的企業、產品、技術,複製的多,原創的少,所以附加值低、可持續性差,中國經濟的整體創新度不夠。
中國人到底有沒有創造力?是中國人本質上不善於創造,還是中國的社會環境制約了中國人的創造力?是中國的經濟制度和社會環境對創新者的激勵不足,對複製者激勵過度,導致中國的企業家群體缺乏創新動力,還是中國企業家在實力上和意識上還沒到創新的階段?近些年來,中國政府開始大力提倡建設創新型國家,大力鼓勵創新、創業,力圖提高中國經濟的創新比重,企業界更是把創新當做競爭發展的第一要義。但是,目前看來效果還不是太明顯。
美國史丹福大學謝德蓀教授這本書對創新提出了一個創造性的框架結構。它最大的啟發是,也許我們中國人對創新的理解太過狹窄,也許我們對創新的理解還停留在麥可·波特的價值鏈理論及五力模型時代,那是一種靜態的、平面的創新(本書稱之為“靜態戰略理論”)。而這本書告訴我們,創新不只是靜態的,也可以是動態的;在資訊時代,企業需要新的“動態戰略理論”。在謝教授看來,創新可以分為“流創新”和“源創新”這兩種方式,波特的理論使企業家把戰略思路都放在產品上也即“流創新”戰略上:降低生產成本、增加供應鏈效益、提高產品的質量、創造產品的差異化、設計產品來迎合細分市場的需求;而“源創新”的著眼點是開拓市場,是從無到有“無中生有”地去建立一個新生態系統,系統內成員通過相互網路來提升各自的價值。中國的企業家們對基於競爭力理論的“流創新”更熟悉,但對與東方“無極”智慧暗合的“源創新”還不太了解。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構建了一種極具操作性的源創新模式,一種與波特的價值鏈理論相對的新型商業模型——“兩面市場商業模型”。
你怎么理解創新,決定著你怎么去創新。解開創新困局的鑰匙,也許就藏在我們的文化基因里。謝教授的這個理論框架對苦陷於“弗里德曼拷問”中的中國企業界和政府界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啟發。從西方出發觸摸東方的智慧,這本書實際上指出了中國人在商業創新上的一個理解誤區。我們既要考慮自己創新得夠不夠,更要考慮自己對創新的理解是否太過狹窄、太過陳舊。如何來定義創新、如何來鑑定創新的方式,也許才是我們首先要思考的問題。中國人或者中國的商業,目前還主要是在產品技術競爭力等“流創新”方面下功夫追趕西方先進,反而忽略了中國文化蘊涵的無中生有式的“源創新”天賦。中國企業可以換一種思路,從波特的價值鏈創新模式里走出來,從“流創新”過渡到“源創新”。
關於中國經濟過去30年崛起的秘密,一直是國際學術界關注的問題。科斯、斯迪格利茨、張五常、林毅夫、周其仁、張維迎、錢穎一等經濟學家,多年來一直在對這個問題進行不同角度的研究。研究過去三十年為什麼成功固然很重要,但評定未來這種奇蹟能否延續、中國人未來能否創新更重要。謝教授的創新理論把這個研究又向前推前了一步。
謝教授能夠提出這套理論,一方面是源於他在史丹福大學多年的研究、積澱,另一方面也是他多年來頻繁奔波於太平洋兩岸,與中國沿海各地有創新企圖和困惑的政府官員、企業家深度交流的結果。作為斯坦福的教授,他主持了很多面向中國企業和官員的關於創新的研修課程,在中美兩國之間架起了一座關於創新交流的橋樑。這本書應該是謝教授多年溝通中美的一個理論收穫,也是迄今為止國際學術界對中國商業創新體系框架的一個全新的研究成果。我們在這本書里,既能看到一個極具啟發性的理論框架,也能看到基於西方經濟史、商業史的大量案例分析,還可以看到對中國企業、中國區域經濟以及中國式創新的評價和思考。我相信,這本書一定會受到中國企業界和經濟界的歡迎。
(作者為《創業家》雜誌社長、創辦人)
引言
引言摘要——
我們看到,如果一個企業只關注它在原有市場的競爭力,而不尋求開拓新市場,必定難以持續發展,因為這種競爭力只能保證它在原有市場的地位。然而,或因科技的進步,或因需求和政策的改變,原有市場會消失或被替代。所以,如果企業只在原有市場發展,最後必然面臨停滯或被淘汰。
在2000年前,商業學者、專家及企業界關注的焦點都是企業的競爭能力,所有有關商業戰略的文獻,都聚焦於建立公司的競爭能力,而影響最深的是著名管理學教授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的價值鏈理論及五力模型。迄今為止,許多企業領導都還沒有注意到,過分注重價值鏈理論,也是造成歷史上很多企業不能持續發展的原因之一。波特的理論及其延伸,都基於一個穩定不變(或緩慢改變)的市場,我稱之為“靜態戰略理論”。近幾十年來,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市場的改變越來越快。在網路時代,市場的生命周期甚至可能少於五年。在這種巨大的變化面前,波特的靜態戰略理論已無法作為企業持久發展的根基。在資訊時代,企業需要全新的“動態戰略理論”,這理論必須根植於不確定且常有變動的市場實際。我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從事動態戰略理論的研究,我將在這本書中向讀者揭示這些研究成果。
動態戰略理論的核心是:在資訊時代,如能善於利用信息,它所提供的價值,會遠比具體產品提供的多。具體產品能提供的價值智慧隨著時間的演變而減少,但隨著時間的演變、信息的增加,我們可以從中提煉的價值也在增加。所以,重點不是在原有的市場競爭,而是隨著信息的增加,如何有效地組合各方成員的資源,來為各方成員創造新價值。這會吸引更多成員加入,而形成一個有生命的生態系統。我因此把它命名為“動態生態系統理論”。在本書中,我把我自創的創新概念與動態戰略理論結合,也特別解析了適應這一動態戰略理論的、與價值鏈相對的一種新型商業模型——兩面市場商業模型。
自2003年我到中國講學開始,我的創新概念與這一動態生態系統理論已經為許多中國的學員所了解與認同,在許多豐富商業實踐的企業家和政府官員那裡產生了強烈共鳴,這也促使我最終決定將這一理論完整展現出來。
書評
“無中生有”才能捅破天
——《源創新》啟示錄
在中國,創新幾乎已經是一個被過度崇拜和詮釋的概念。但另一方面,你又會奇怪地發現,身邊真正的創新卻不多見。
這就像一個奇怪的悖論——創新被推上了神壇,然而大部分人卻選擇繞道走。或者說,打著創新的旗號,幹著模仿的勾當。當然,我並不是說模仿是壞事。我想說的是,我們其實還可以做得更多。往大處說,“中國製造”在越來越強的資源約束下面臨的困境,必須服創新這劑解藥。往小處說,商界一城一池之得失,一個公司的生死存亡,也必須直面創新的刀鋒兩面。
所以,如果一定要我說一句,我寧願說,“路子野一點吧,從紅海殺到藍海去!”我所認識的大洋彼岸的謝德蓀(Edison Tse)教授是個溫文爾雅的學者,但讓我驚喜的是,他多年心血所凝聚的新作《源創新》,稱得上殺氣逼人。令人精神一凜。
謝教授集多種武功於一身——長期在矽谷的中心地帶史丹福大學,對新技術浪潮和各種商業實體的起伏有準確而獨到的觀察;多年往返於美中兩國,桃李遍布國內政府界和商界,對中國國情有自己的理解;自身參與創辦了多家企業,實踐經驗豐富。畫外人看畫,心中自有峰和嶺。多年厚積薄發,謝教授開闢了一個創新的理論框架,命名為“源創新”。
在他看來,創新可分為“流創新”和“源創新”兩種方式。大家所熟知的邁爾克▪波特的理論使企業家把戰略思路放在產品上,可稱之為“流創新”戰略——降低生產成本、增加供應鏈效益、提高產品的質量、創造產品的差異化、設計產品來迎合細分市場的需求。此種“流創新”當然有作用,但弊端亦很明顯——價值鏈某一環節的企業可用流創新來維持它的競爭能力,它的淨利潤也會因創新而增加,但它的競爭對手也會很快跟上並使淨利潤隨之下降。所以,不論在哪一環節,流創新所造成的優勢都難以持久。於是,要維持競爭優勢,企業需要頻繁地進行流創新,但這不僅會增加創新的成本,而且在同一環節經常進行創新活動會造成回報遞減,由此所獲的淨利潤率也逐漸降低。而“源創新”的著眼點是開拓市場,是“無中生有”地去建立一個新生態系統,系統內成員通過相互網路來提升各自的價值。 謝教授認為“源創新”其實非常適合在中國的土壤上開枝散葉。源創新能力包括對人的欲望的理解能力、建立關係網的能力、有創意模仿的能力及執行的能力,而這些都跟中國的傳統、文化結構及環境吻合。在更具體的層面,謝教授指出,源創新由兩個要素組成,Grabber和Holder。Grabber是一個可以在感性層面觸動人心的理念;Holder是可以使人從中得到真實利益的實體,是理念背後的支持系統。兩者若能齊頭並進,則一個新的生態系統有望成型。
謝教授開闢理論框架的功夫了得,而更難得是,書中對於諸多商業案例順手拈來:雅虎、google、索尼、JVC等等,商場上的成敗得失放入“源創新”的框架之中,不少疑惑之處赫然開朗。
謝教授是個溫文爾雅的人,但讀完此書,我覺得他真正想說的是,“兄弟們,路子野一點吧,從紅海殺到藍海去!”
譚昊 《理財周報》副主編
書評2
從“Made in China”到“Made for China”
——《源創新》:轉型期中國企業創新之道
雖然建立創新型社會的呼聲很高,但大多數中國企業創新能力不強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很多學者專家都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及企業管理方法成了中國創新的包袱,使中國企業難以建立創新能力。但《源創新》一書的作者---美國史丹福大學謝德蓀教授卻認為,中國企業實際上有著很強的創新潛力,之所以還沒有在創新上取得成功,是因為他們在思考這一問題的出發點上就陷入了誤區。
這一誤區在很多中國企業的創新過程中都有著體現。比如,許多企業都以科技領先為公司的戰略重點。在技術研發上投入大量精力並獲得很多專利。但這些專利並沒有對企業發展起到實際的推動作用。又比如,很多企業面臨發展停滯時,都希望通過產品創新來取得突破,但新產品雖然在短期內為企業帶來了效益,但隨著後來者的模仿、複製和超越,這種優勢很快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喪失。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謝德蓀教授認為這是人們對創新的認識不足造成的,他提出,首先要對幾類不同的“創新”加以區分:科學創新是指有關大自然規律的新發現,包括新科學理論及新科技,在《源創新》一書中,這種創新被稱為始創新。商業創新是相對於科技創新來說的,商業創新是指可創造新價值的創新行為,又可細分為流創新與源創新兩類。流創新是以自身資源和力量來滿足現在市場的需求來增加價值,這包括新產品、新生產流程及降低成本等。源創新是指推動新理念價值,引導其他相關成員加入,組合大家的資源與能力來滿足人的欲望,藉此開拓新市場。
謝德蓀教授在《源創新》一書中回答了上述問題:中國的大多數企業都力圖在始創新能力和流創新能力上爭取競爭優勢。但實際上始創新本身沒有使用價值,先進的科技只能是創造價值的前提條件,是否能真正轉化為價值還要取決於企業的商業創新能力。因為也就是說,企業的競爭優勢,並不是基於它的科技,而是基於它能套用科技來創造多大的新價值。只有擁有流創新或源創新能力的企業能夠將其轉化為價值。但是如果價值是通過流創新來實現的,那么企業雖然能夠在短期內享有優勢,但這種優勢不能持久。所以,謝德蓀教授認為,對於企業發展來說,源創新遠遠比始創新和流創新更重要。
讀到這裡,我們才恍然大悟,通過科技創新和產品創新來幫助企業走出困境,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因為兩者都仍然是以產品為中心的傳統價值鏈下的創新,是工業革命時代思維的衍生物。但在步入資訊時代後,麥可.波特的傳統價值鏈商業模型早已不足以描述資訊時代市場高速變動情況下的經濟活動,更無法為“源創新”制定戰略依據。
在《源創新》一書中,謝德蓀教授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更適合資訊時代的商業模型:“兩面市場商業模型”。在兩面市場商業模型中,“客戶”的概念不單指企業銷售產品或服務的對象,還包括支持企業的所有相關成員,比如上游的供應商。企業是這兩面客戶間的平台,它的主要戰略是如何組合一面市場成員的資源及能力來提供價值給另一面市場的客戶,平台管理兩面互動使雙方所得到的價值越來越大,平台獲得的回報也越大。在本書中,謝德蓀教授用多種不同的行業案例描述了兩面市場模型的特徵;兩面市場模型與價值鏈模型的差異;多種建築兩面市場模型的方法;企業如何套用它以源創新戰略來取得突破、開拓新市場、轉危為安及持續發展。可以說,兩面市場模型是策劃源創新戰略的基礎,也是本書的重點。
現在世界已進入信息革命時代,而正如謝教授所指出的,中國的很多企業仍然停留在工業革命時代的舊思維里,在創新之路上舉步維艱。因此,《源創新》提出,中國經濟的轉型一定要從工業革命思維的“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 轉為信息革命思維的“為中國製造”(Made for China),通過研究中國市場消費者的欲求和需要,有更多成功的源創新,才能真正啟動內需市場。我相信,這本書定會給中國的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學者帶來很多有益啟迪。
書摘
第一章 《創新之論》選摘——
“中國製造”面臨著幾個嚴重問題。第一,隨著工資增加,競爭也越來越激烈。第二,能源消耗大,引起了一些環境問題。如果我們將環保消耗算進成本,可能總利潤是負數。中國的製造經濟不可能長久這樣不計環境成本。第三,國際對中國出品有一些不好的印象,認為中國的製造不負責任,如“玩具”、“奶粉事件”。我曾在美國看到了一個廣告“我們不賣任何中國製造的產品”,商家以此來吸引顧客。第四,來自國際的壓力。有些國家告我們傾銷,如“輪胎事件”。其實我們的出口並沒有對其他國家的工人就業產生多大的影響,但是很多人覺得我們的出口太多了,就產生反感。第五,世界經濟蕭條。2008 年以後的金融危機、歐債危機使美、歐消費市場下降,中國很多地區在2008 年已經感受到了這個情況。第六,規模越大,面臨的危機越大。那么多的廠房與機器,沒有生意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在2009 年,中國很多工廠都因世界金融風暴而倒閉。
事實上,以上提到的不是一個單一的製造業的問題,也不是哪一個行業的問題,這是整個行業及整箇中國所面臨的問題。解決個別企業的眼前困難不能只解決基本問題,而需要有系統性措施,才能使大家轉危為安。
很多學者與專家都認為創新能使中國走出它所面臨的困境,但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創新”,尤其是中國的創新呢?
歐美的企業創新通常是由個人開始而後帶動他人加入,所以一個企業的創新能力以其員工的創新能力為基礎。歐美人普遍認為一個人要有創新能力,他必須有遠見、有熱情,敢想他人不敢想的事,不墨守成規而且能向傳統智慧挑戰,有勇氣承擔風險,有能力說服他人。因為中國企業有員工服從於領導的文化,中國員工有著很強的執行能力及模仿能力,卻並不習慣向傳統智慧挑戰,所以很多歐美學者都認為中國企業的員工缺少創新能力,中國企業在現狀下也難以創新。
有一次,我帶一個中國企業領袖團到一家美國公認最有創意的公司考察。這間公司名叫IDEO,位於史丹福大學附近,它的創始人是史丹福大學的教授,其主要業務是為很多大公司設計創新產品及提供創新顧問。這家公司的戰略是聘請一批很有創意的員工,然後讓他們自由發展,公司只提供信息及設計上的支持,例如一個很豐富的產品資料庫,一個包羅萬有的實驗室。領袖團成員看到這家公司所完成的各種各樣的創新設計產品,都感到驚訝和欽佩。其中一位用國語問我:“謝教授,它的經理們如何給員工定指標?如何對員工進行考核?”我把問題翻譯為英語向該公司的一位經理請教,這經理回答說,他們對員工沒有指標也沒有考核,公司只看員工的成果,經理的主要工作是作員工的教練,引導員工的思路。提問的領袖說:“這怎么可能,那公司不是亂套了嗎?在中國肯定不行。”
我認為中國要建立創新能力,雖然不一定要做到與IDEO 一樣,但也必須從根本上有思路的改變。中國企業創新不一定要走歐美企業的道路,而應該跟中國的傳統、文化結構與社會環境相結合。
讓我們來認真分析一下“創新”和創新活動。
在很多人的觀念里,創新幾乎等同於高科技,認為生產高科技產品便是創新。現有的評價體系,也通常以一個企業或一個國家一年獲得專利的數量來衡量它的創新程度。一個新產品可以因為它的特殊設計有異於當前產品而獲得專利,一項新科技可以因為它有異於當前的科技而獲得專利,一道新的生產流程可以因為它有一些新的特殊的程式而獲得專利,它們的共同點在於有異於當前,而且可增加價值。因此,很多歐美學者認為創新是開發新產品、發明新科技,或建立新生產流程。
我認為,以企業一年內獲得專利的數量來衡量它的創新程度太狹窄了,而且是錯誤的。據統計,只有很少的專利能給公司帶來財富,大部分的專利都不能為公司產生價值。這不是說專利是廢物,只不過說明公司市值高低不能用專利多少來衡量。
那么,對一個企業而言,到底什麼是創新?是不是做新產品便是創新?例如一個企業開發新的產品,但是產品投入生產後發現沒有市場,這是不是有意義的創新?我的意見是,對一個企業來說,那些不能使企業得到淨效益的創新活動都是浪費。
第四章 《商業模型的創新:兩面市場》選摘——
採用價值鏈模型與兩面市場模型的企業對客戶的認識程度是不一樣的。在價值鏈模型中,企業最關注的是如何拓展它的產品市場,因此它要了解每一個市段的客戶對它產品的需求。如果某一市段的客戶對它現有的產品需求不高,那么它就會“揣測”客戶的需求並通過提供服務或增加其他配件以使客戶得到更滿意的產品,所以它對客戶的認識局限於客戶對企業出售的產品的需求。但在兩面市場商業模型中,企業最關注的是組合一面市場成員的資源及能力來提供價值給另一面市場的客戶,因此它需要認識及了解每一面客戶在生活與工作上的習慣、需求、欲望以及他們的資源及能力。所以,兩面市場模型對客戶認識及了解的程度遠遠超過價值鏈模型對客戶的認識及了解。
在第一章,我強調創新是創造新價值。一個企業的理念價值是創新的前提,價值鏈模型的新理念價值有關產品的質量及功能、生產流程、市場推銷、倉庫及供應鏈管理,價值鏈模型是流創新的基礎;而兩面市場的新理念有關啟發及滿足其中一面客戶的需求及欲望,這往往需要超越客戶現在的需求,要建立一個新的生態系統才能實現這樣的新理念,而這個生態系統最少有兩條價值鏈互動而造成網路效應,所以兩面市場模型是源創新的基礎。
這兩個商業模型可以說是對立的,因此支持這兩個商業模型的生態系統也是不同而且是對立的。支持價值鏈的生態系統很快便靜止,而支持兩面市場的生態系統以指數上升。因此如果兩個競爭企業,一個是採用價值鏈商業模型來建立流創新戰略,而另一個是採取兩面市場商業模型來建立源創新戰略,那么勝利者必然是採用兩面市場商業模型的企業。如果在位者採用價值鏈商業模型,那么後來者一定可以採取兩面市場商業模型來取代在位者的地位。
價值鏈商業模型核心競爭力的根源是產品設計、生產成本、市場份額、滿足客戶需求的效率,這些活動都以產品為核心,所以採用價值鏈商業模型的企業實施的是產品中心化戰略。兩面市場商業模型競爭能力的根源是了解兩面客戶的欲望及能力,組合自身及一面客戶的資源及能力來滿足另一面的欲望。這些活動都是以兩面客戶為核心,所以採用兩面市場商業模型的企業實施的是客戶中心化戰略。
第十章《中國轉型及中國創新之路》選摘——
從第九章我們看到,矽谷在上世紀50年代還是農業地區,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才慢慢變為美國科技自主創新並套用於源創新的中心。從這一過程中,我們看到很重要的四點:(1)若沒有一個好的創新環境就很難吸引或培養一群有創意的人;(2)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可使始創者得到利益,有效鼓勵創新活動;(3)只有科技創新而沒有源創新能力的配合是不能創造新價值的,因為這使始創者得不到很大的好處,將打擊後來者創新的積極性;(4)如果要使科技創新成為地區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這一地區必須有比較完整的持續創新生態系統。
這也就是說,自主創新需要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及有源創新能力來配合,如此才能得到大收穫。中國現在推行自主創新,但如沒有嚴格執行智慧財產權的保護,這些創新活動就都不能得到投資者支持,尤其是發展知識密集的產品,如文化內容、新軟體技術等。因為源創新注重的是知識的價值,沒有嚴格執行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會影響源創新執行的效力。所以我認為嚴格執行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是國家首要的任務。
自主創新為的是要減少與世界最先進科技的距離,但這需要很長時間。在這一時段,中國可先從外國引進新科技,再加以改良以適應中國的環境,利用這種新科技來幫助現在的傳統企業進行源創新,以此幫助中國企業建立開拓新市場的能力。同時,中國在多個地區創造好的創新環境,建立機制鼓勵有質量的源創新風投群體成立。那么多年後,中國便將具備以上說的四個條件,從而使科技創新及自主創新能不斷提供新機會來推動源創新。在這期間,中國的經濟也將慢慢從生產經濟轉變為創新經濟。這種轉變不是一個企業的轉變,而是多個地區、整個國家的轉變。這不僅徹底解決了現在中國製造業面臨的問題,而且也使中國開拓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途徑。
中國有很多強大的國有企業及國家控股公司,它們很多都擁有國家獨有資源,它們可進行壟斷,短期獲取巨大利益,但這不能持久,因為它們沒有不斷創造新價值,而且會造成貧富差距,引致社會不安定;但它們也可以這些獨有資源為支點,引導其他流創新企業加入,共同推動源創新價值理念。在此過程中,不只加強自己的生態系統,而且使很多相關行業都能發展,共同做到和諧發展。我們看到中國移動在2001年便善用它的獨有資源,推動夢網,以整合中國移動與網際網路公司資源來提供新價值。這不僅加強了中國移動的生態系統,也救活了新浪、騰訊、搜狐等網路公司,進而成就了以後整個網路產業。所以,如果擁有國家獨有資源的企業的領袖能對源創新有深認識,他可以領導採取戰略來有效地推動源創新,以此來帶動其他在它生態系統內的企業以流創新來支持,而做成整個生態系統的和諧發展。中國政府可建立機制來鼓勵擁有國家獨有資源的企業,以源創新與流創新的互動為它們發展的推動力,來達到國家的和諧發展。一個可能的機制是以該企業的生態系統成員(連自己在內)的數量及它們的總收入為該企業的業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