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資訊
作 者:曾昭奮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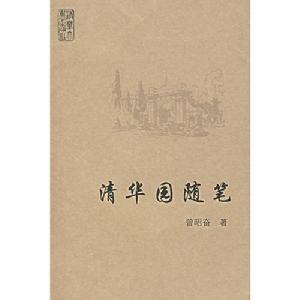 《清華園隨筆》封面
《清華園隨筆》封面出版時間:2004-4-1
版 次:1
頁 數:247
字 數:186000
印刷時間:2007-5-1
紙 張:膠版紙
I S B N:9787302083238
包 裝:平裝
內容簡介
本書是清華大學建築系曾昭奮先生近年來已發表和未發表的雜文隨筆集。書的主體部分是作者以歷年清華校慶為契機寫的十篇高質量的隨筆,多數曾發表於《讀書》雜誌。這些隨筆和雜文圍繞與清華有關的人、事、物展開,或針砭時弊,或懷念故人,筆觸或凌厲,或深情,無不是款款道來,韻味深長,閱後難忘。全書圖文並茂,文筆深入淺出,清新雋永,能給予讀者非一般的精神享受。
作者簡介
曾昭奮: 中外建築界著名評論家、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著名的歸僑教授、建築評論家、原《世界建築》主編和圓明園研究專家。
曾任《世界建築》雜誌副主編6年,主編10年。作為他生活的主要內容,《世界建築》伴隨了曾昭奮走過16年的時間。
1995年曾昭奮退休,距今已達10年。說起今日早已成為建築行業專業核心期刊的《世界建築》,他就像是說起一個已經長大成人的孩子,驕傲,有所牽掛,但不再干涉:“退休後就不再管事務了。偶爾看看。現在雜誌有廣告,經濟條件比較好,工作人員也多,不像當年那么辛苦。”
曾昭奮所說的:“做了多年的《世界建築》雜誌編輯工作,對它向讀者推介的每一個名建築,對它的讀者們,都有一種感情在。我把這種感情,叫做《世界建築》情結,一個老編輯的建築情結,未知當否。”
作品目錄
清華園裡可讀書?——校慶隨筆之一
第十二座雕像——校慶隨筆之二
清芬正氣傳當世——校慶隨筆之三
圖書館靜悄悄——校慶隨筆之四
科學春秋——校慶隨筆之五
散步清華園——校慶隨筆之六
後搖籃曲——校慶隨筆之七
大樓與書桌——校慶隨筆之八
江河萬里——校慶隨筆之九
江河萬里(未刊部分)
芳草萋萋憶仙洲——校慶隨筆之十
公共藝術的空間有多大?——校慶隨筆之十一
從北京到南通——校慶隨筆之十二
家在藍旗營——校慶隨筆之十三
一代大師出梁門——梁思成先生創建清華大學建築系五十周年
永遠的圓明園——圓明園罹難140周年祭
國家大劇院設計和使用過程的民主性
百年北大的兩幢新建築
風貌長宜放眼量——談北京的“風貌建築”和“古都風貌”
西單有廣場
西客站的故事
評大觀園酒店和北京西客站
附錄1 梁思成給車金銘的一封信
附錄2 平實的道理,清新的氣息——讀梁思成先生給車金銘專員的一封信
附錄3 北園酒家、梁啓超紀念館和梁思成先生的一次演講——紀念梁思成先生誕辰100周年
作品選讀
今年四月三十日,清華大學八十四周年校慶。清華名教授,建築學家梁思成先生的銅像在剛落成的建築館中揭幕。揭幕典禮的幾百名參加者,梁先生的親人、朋友、弟子,外地趕來的校友和在學的學生,擠滿了新館入口的正廳和側廳。
這是安放在清華園各室內外公共場所中的第十二座雕像。梁先生好像剛從家裡來到系裡上班。他所特有的愛說話愛議論、親切近人、風趣俏皮的神情卻沒有留下多少。
梁先生是一九七二年在一片寂寞中去世的。但是,作為一個學者,一個社會活動家,他在逝世前很久就已經沒有說話了。——《梁思成文集》最後一卷(第四卷)的最後一篇文章,寫於一九六四年七月。
我第一次聽梁先生講話是在一九五九年冬天。那時他從北京來到故鄉廣東。我們學校學生會請他到我所在的班級發表演說。梁先生談到多年來黨對他的思想、學術和病弱的身體無微不至的醫治和關心。他說這些話的時候,就像一個天真的兒童在傾訴著如何感激如何愛戴自己的母親,完全不像一位年近花甲的著名學者。接著,梁先生講到建國十年的偉大建設成就,講到首都十大建築的成功創作。當他談到北京的城牆和城樓時,他繼續激動著。他說:“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牆,就像剝掉我的一層皮。”在我們這些經過“反右”運動的大學生聽來,這話比“右派”還要右。後來到了清華,才知道梁先生曾在不同的場合,說過這相同的話。——然而,在《梁思成文集》中,卻沒有這段文字。
五十年前,二次大戰快結束時,梁先生在重慶,曾寫信給美軍有關人士,希望美軍在對日本本土實施轟炸時,對奈良和京都這兩座文化古城手下留情。
也是五十年前,梁先生作為中國的代表,作為中國建築師,參加了聯合國大廈的設計工作。
四十九年前,梁先生在清華大學創建了建築系。
四十七年前,當時“和平解放北平”的談判尚無結果。人民解放軍的代表來到清華園梁家,表示萬一和談破裂不得不以武力攻城時,須對城內的古建築等實行保護,請梁先生在軍用地圖上標出它們的位置。
這幾件事,對一位建築學家來說,對於我們建築界來說,都是大事。但是,翻遍《梁思成文集》,都沒有見到任何記載。
四十六年前,人民共和國定都北京。梁先生偕同陳占祥先生,提出了保護北京舊城、在西郊逐步建設新的行政中心的建議和規劃設計方案。(《梁思成文集》第四卷)那時節,進行大規模新區建設一時確非國力所允許,然而,保護舊城的願望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舊城保護不成,梁先生退而求其末——保留舊城的城牆和城樓。於是,在《梁思成文集》第四卷中,留下了動情的文字:
城牆上面,平均寬度約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薔薇一類的灌木,或鋪些草地,種植草花,再安放些園椅。夏季黃昏,可供數十萬人的納涼游息。秋高氣爽的時節,登高遠眺,俯視全城,西北蒼蒼的西山,東南無際的平原,居住於城市的人民可以這樣接近大自然,胸襟壯闊。還有城樓角樓等可以闢為陳列館,閱覽室,茶點鋪。這樣一帶環城的文娛圈,環城立體公園,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古老的城牆正在等候著負起新的任務,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周,等候著為人民服務,休息他們的疲勞筋骨,培養他們的優美情緒,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來豐富他們的生活。
它將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園之一——一個全長達39.75公里的立體環城公園!”
然而,急速前進的歷史和城市首腦的匆忙決策,徹底淹沒了梁先生熱情的建議和童話般的憧憬。有一天,梁先生從城內開完會回到系裡,談到了北京市負責人的話:“誰要是再反對拆城牆,是黨員就開除他的黨籍!”從此,反對的意見,美好的建議,都沉默了,舉世無雙的城牆和城樓,也就慢慢地被拆光了。
作為一個建築學家,繼而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梁先生早把自己的生命和情感與北京城融合在一起了。他為之奔走呼號,為之陳情請命的古都北京,作為一個整體,是保不住了,最後,連城牆城樓也保不住了,就連反對的意見也不能說了。但是,他最後還剩下“喊痛”(剜肉切膚之痛)的權利和機會——這在當時,的的確確是一種難以聽到的、非常勇敢的聲音,一種在繼續“反對”的呼喊。
然而,梁先生也許沒有理解:整個兒的一座兩座古城,在即將落下炸彈之前可望得到保護;一個偉大的文化古都,在攻城的炮彈尚未發射時可以獲得關懷;而一線城牆,卻連“保護”的意見也不能再說,只能眼巴巴看著它在和平時期里徹底地消失。
歷史過早地為梁先生鑄就了這緘默的雕像。
當人們爭先恐後在梁先生銅像前面照相留念時,在熙攘嘈雜中,在閒聊中,在不到十分鐘時間裡,就有兩位朋友直著嗓子對我說了同一內容的話:北京市某位負責人引咎辭職,“北京不會再蓋那么多大屋頂了。”這時人們已經忘卻五十年代中期批判建築創作中的復古主義的情景和當時梁先生的處境。因為人們明白,近年來北京建設中空前繁榮興旺的大屋頂,已經跟梁先生沒有必然的聯繫,而是北京所提出的“維護古都風貌”和“奪回古都風貌”的方針及其具體操作的直接後果。
今年年初,首都舉辦了一個以“奪回古都風貌,繁榮建築創作”為題的建築設計展。門口的觀眾留言簿上,寫得最多的是對大屋頂大肆泛濫的不滿和質問,跟展覽會舉辦者對許多蓋著琉璃瓦大屋頂和皇亭子的星級飯店之類所加的“民族傳統、地方特色、時代精神”的贊語唱反調。繼續參觀,人們還可以看到不少建築物的“原始方案”和“實施方案”同台展出:前者是一些平頂的比較現代化的建築,後者卻一律被不問情由、不問造價地扣上大小不同的琉璃瓦頂子。就像作家寫的小說,被硬安上一個“光明的尾巴”。建築創作的成果被篡改了,建築師任何新的探索和對建築藝術形式的任何新的追求,以及建築創作中的民主和自由,統統被壓制了——這些從建築創作過程以外強加的東西!
從五六十年代拆城牆拆城樓,到八九十年代大蓋假古董偽劣大屋頂,一個是拆除古蹟,一個是假造舊貌,是兩個不同的事件。但都發生在一個城市中,並且同樣以不準反對、不準異議的獨斷方式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