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五四前後,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為代表的西化論者和以杜亞泉、章士釗、梁啓超、梁漱溟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圍繞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比較、新舊文化的關係看待和中國文化出路的選擇等問題,展開了一場延續十餘年的思想大論戰。這場論戰的實質是中國封建舊文化和西方資產階級新文化的鬥爭,也可以說是清末以來中學、西學之爭的繼續。它發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帶有許多新的特點,對後來中國文化的走向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
論戰的歷史背景
五四時期東西文化論戰的發生不是偶然的,當時的政治腐敗、經濟落後和社會黑暗是它產生的直接原因。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帝制,為中國這個東方古國走向現代化提供了契機,但由於沒有從政治、經濟上徹底摧毀封建專制主義統治,更沒有在思想文化領域剷除封建勢力的根基,辛亥革命的成果只是曇花一現。辛亥革命後,伴隨封建帝制的復辟,在思想文化領域裡又出現了一股尊孔復古的逆流。民主共和的命運會怎樣?國家的出路在哪裡?迫切要求人們進行思考和作出回答。在此背景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激進知識分子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竭力宣揚西洋近代資本主義文化,向腐朽的封建思想文化展開了猛烈的衝擊,由此引發了這次東西文化論戰。
論戰歷程
第一階段
1915~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由於新文化運動剛剛興起,當時關於東西文化的爭論,基本上是延續前人的問題展開的。討論主要集中於比較東西文化優劣方面,羅列各種現象,從而引申出東西文明的異同。這是這一階段的基本特點。當時爭論主要在以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為主力的《新青年》與杜亞泉(傖父)任主編的《東方雜誌》間展開,蔡元培、毛子水等也加入了論爭。舊派學人的代表辜鴻銘寫了《春秋大義》一文,鼓吹尊王、尊孔,宣揚中國國有文化,認為西方文化不如中國文化,反對西方文化的輸入。《東方雜誌》發表一系列文章支持辜鴻銘的觀點。陳獨秀先後發表《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批判《東方雜誌》維護君道臣節、名教綱常等封建制度與封建倫理、反對西方文化的立場,基本闡明了新舊文化、東西文化的根本區別與優劣。李大釗寫了《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肯定西洋文明比東方文明優越,中國的唯一出路是積極吸收西方文化,徹底否定中國固有的封建文化。
第二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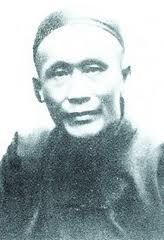 杜亞泉
杜亞泉1919~1921年。東西文化能否調和是這一時期爭論的焦點。由比較東西文化的差異發展為如何處理東西文化間的關係,進而東西文化之爭又轉化為新的文化問題之爭,從討論兩者關係引申為辯論新舊文化的能否融合。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張東蓀、陳嘉異、章士釗、蔣夢麟、常乃惪等。其間,林琴南曾運動國會議員彈劾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蔡元培發表《致公言報並答林琴南君》,表明他堅持"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陳獨秀、李大釗等反對以政治干涉學術,以武力壓制新思想,提出要正確處理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學術問題應平心靜氣地進行討論,思想以愈辯而愈新,真理以愈辯而愈明。
西化論者認為,西洋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是兩種性質截然相反的文化,存在新舊之分,是水火不容的;中國的舊文化在古代雖然有它的價值,但到了現代則成了過時的東西,已失去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因此他們從新勝於舊,今勝於古的前提出發,反對新舊調和,反對保存舊的文化傳統,而主張破舊立新、以新代舊。
章士釗等東方文化派則認為,新舊是一個歷史的範疇,其涵義因時、因地和內容的變化而異,所以對文化之優劣的評判,不能僅僅以新或舊為標準,不能以新舊來區分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他們認為,就文化演化的趨向而言,也是新中有舊,舊中有新,是一個由新而舊、由舊而新的遞嬗過程,新舊不能也無法分開,新是舊的發展,舊是新的根基,沒有舊也沒有新。所以東方文化派認為,西化論者反對新舊調和、反對繼承傳統文化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中西文化彼此難分優劣,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因此中國文化的出路,只能是“一面開新,一面復舊”,取西方文化之長,補中國文化之短,實現中西文化的折衷調和。
第三階段
1921~1927年。梁啓超《歐遊心影錄》與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相繼發表,使東西文化之爭進入一個新高潮。雖然從表面看這一時期爭論重點重又回到東西文化優劣比較的老問題上,但論戰的深度已大大前進了一步,涉及面也大大超過了從前,並且開始關注東西文化如何結合的實踐問題。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梁啓超、梁漱溟、馮友蘭、張東蓀、胡適、瞿秋白、郭沫若、孤桐等人。
這場大論爭儘管無法解決提出的所有問題,但爭論本身則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為中國科學與民主觀念的深入人心作出了貢獻。
論戰的評價
 五四前後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
五四前後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五四前後東方文化派與新文化派關於東西方文化的論戰,涉及的問題非常廣泛,但就其整個論戰的過程而言,主要爭論的是東西文化的差異比較、新舊文化的關係看待和中國文化出路的選擇這三個問題。因此,這次論戰實質上是要不要向西方(後來包括俄國)學習、如何學習以及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
在這場中西文化問題的論爭中,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批判舊思想、舊文化,其主流無疑是正確的,體現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方向。這場運動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給封建主義以空前的沉重打擊,破除了封建教條對人們思想的束縛,對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青年的覺醒起了巨大作用。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高潮,他促進了人們更加迫切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而保守派則站在它的的對立面加以反對,鼓吹尊孔讀經,維護儒家的文化傳統,從根本上說是錯誤的,是逆潮流而動的。但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也存在著絕對化、簡單化的缺點和錯誤,他們強調文化的時代性和不同社會發展成都的差異性,但忽視甚至否認文化的傳承性和民族性。杜亞泉等東方文化派看到了文化的傳承性和民族性,但忽視甚至否認文化的時代性和不同社會發展的差異性。這都是缺乏科學的分析態度,因此,激烈的論證並沒有使問題得到真正解決。
中西文化問題是近代中國社會出現的一個重要問題,它受到各派人士的關注。對於這個問題的爭論連續不斷,可以說伴隨著整個近代的歷史進程可,反映了近代歷史的發展變化。在五四運動以前,中西文化問題的論證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主義舊文化的鬥爭,是如何看待中國固有文化和西方文化,建設中國近代文化的問題。在爭論過程中,人們的認識逐步深化,但問題並沒有解決。五四運動後,中西文化問題的爭論更加廣泛地展開。
李大釗與“五四”前後東西文化論戰
 李大釗
李大釗“五四”前後的東西文化論戰,從1915年到1927年延續10餘年,參加者數百人,發表文章近千篇,專著數十種,是近代中國東西文化問題論戰的高潮,關係到中國社會變革的性質和方向。李大釗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發表直接參加討論的文章並不很多,但他提出了不少十分深刻的觀點,成為論戰中不可忽視的人物。因此,對他在論戰中所起的作用進行若干探討,是不無現實意義的。
(一)五四時期的東西文化論戰,是繼中國近代史上洋務與守舊、維新與洋務、革命與立憲之爭而起的,但又與這些論爭的思想內容有所不同。它不僅要求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政治制度,而且要求學習西方的文化想思、倫理道德,即意識形態的一切領域,以“改造國民性”。這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們認為,辛亥革命之所以終於失敗,就因為缺少這樣一場文化思想上的革命。如陳獨秀就說:“蓋論理問題不解決,則政治(按:指制度)學術(按:指技藝),皆枝葉問題。縱一時舍舊謀新,而根本思想未嘗變更,不鏇踵而仍復舊觀者,此自然必然之爭也。”於是,他們就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向著中國封建文化傳統猛烈轟擊,要求人們從沿襲幾千年的孔夫子宗教教條統治下解放出來。這就拉開了五四時期東西文化論戰的序幕。
如果說,在前此關於文化問題的論爭中,對外來的西方文化,守舊派往往採取驕矜唾罵、深閉固拒的態度,到了“五四”前夜,這種簡單的排外主義辦法已沒有多少市場,堅持這樣做的人固然還有辜鴻銘、林琴南等,但更多的守舊人士卻改變了策略,從表面上看他們似乎持平公允,實際上則是封建文化衛道士的花樣翻新。當時《東方雜誌》的主編杜亞泉,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他用傖父的筆名,發表了如《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迷亂之現代人心》等多篇文章。他毫不諱言道:當時若“僅僅效從頑固黨之所為,竭力防遏西洋學說之輸入,不但勢有所不能、抑亦無濟於事”。問題是怎樣去評價東西文明的優劣並實行相互的“取長補短”。他認為:“精神文明之優劣,不能以富強與否為標準”,西洋人於“物質上雖獲成功”,但“其精神上之煩悶殊甚”。相反地,中國社會在物質上抱“不飢不寒,養生喪死無憾”,精神上“確信”我國“固有之道德觀念,為最純粹最中正者”。換言之,即“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這兩種文明的優劣若何?他認為,大“凡社會之中,不可不以靜為基礎”,故西洋“動”的文明需依靠中國“靜”的文明以救弊。只有用儒學來統整世界文明,中國和“全世界之救濟亦在於是”。這種復古派的言論,不能不激起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猛力反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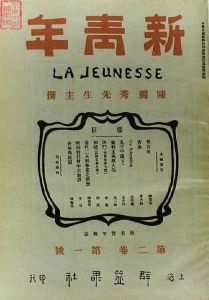 新青年
新青年陳獨秀在《新青年》雜誌連續發表了《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等文章,對上述論點展開了系統的抨擊。他首先從三方面闡述了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和優劣:第一,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為本位,所以成為“雍容文雅之劣等”民族。第二,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宗法制度造成“種種卑劣不法,慘酷衰微之象”。第三,西洋民族以法治為本位;東洋民族以感情為本位,施之者“多外飾厚情,內恆憤忌”,受之者“習為貪惰,自促其生以弱其群”。應當怎樣來判斷這兩種文明的優劣?陳獨秀提出一個簡單的道理質問道:“古今中外之禮法制度”,“有一不直接或間接為穿衣吃飯而設”呢?從《東方》雜誌記者的言論中也可以看出穿衣吃飯問題的被重視,這豈非與“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相衝突?因此,西方文明肯定要比東方文明先進,中國文化“若是決計榮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這些,表明陳獨秀對中國封建文化傳統的不可調和性。同時,也反映了他的不問國情、要求一切西化的傾向。
1917年4月,李大釗刊布《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1918年7月又發表了《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等文。首先,在怎樣認識東西文明的區分及其優劣的問題上,李大釗固然也把兩種文明概括為“靜”與“動”的區別,即東方文明是“靜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動的文明”。但是,他認為造成這兩種文明區分的根源固然是複雜的,不僅有地理環境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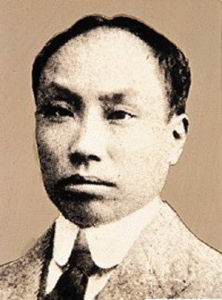 陳獨秀
陳獨秀化背景的不同,“而其最要之點,則在東西民族之祖先,其生活之依據不同”。東方生計“以農業為主”,西方生計“以工商為主”。由於這兩種經濟生活的區別,由此從思想、哲學、宗教、倫理、政治等方面推演出幾十項關於兩種文明的具體差異。這兩種文明進化到了今天,我國“靜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從處於屈敗之勢”,西洋“動的文明,物質的生活”,“實屬優越之域”。整個社會絕不是“以靜為基礎”,而是出現了“動”的潮流。“例如火車輪船之不能不乘,電燈電話之不能不用,個性自由之不能不要求,代議政治之不能不採行。凡此種種,要足以證吾人生活之領域,確為動的文明物質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勢滔滔,殆不可遏”。在這“動”的潮流面前,若“守靜的態度,持靜的觀念,以臨動的生活,必至人身與器物,國家與制度,都歸粉碎”。他形象地指出,“蓋以半死帶活之人,駕飛行艇,使發昏帶醉之徒,御機車,人固死於艇車之下,艇車亦毀於其人之手”。換句話說,當今不是西洋“動”的文明依靠中國“靜“的文明以濟窮救弊,而是須要“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長,以濟吾靜止文明之窮”。
李大釗要求中國吸收西方文化,並不是不講國情、主張一切西化的觀點。在他看來,西洋文明本身雖已開始走下坡路,但比我國文明優越,仍值得學習:“彼西洋之動的文明,物質的生活,雖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無趨於自殺之傾向,而以臨於吾儕,則實居優越之域”。同時,學習西方文化,不要求一切“取法西洋”,只以自身之短學別人之長,堅決反對盲目的排外主義。
李大釗主張中國應當吸取西洋先進文明的特長,以濟我固有文明的窮困,這不是說中國固有文明一無是處。李大釗對復古派如何崇拜儒家孔學,作了系統的剖析。在他看來:(一)孔子生於春秋末期,“自不能不以當時的政治制度立說”。但由於時代於變遷,適應於當時條件下產生的一套倫理學說,已經無法適應於現代生活,故“孔子之於今日之吾人,非殘骸枯骨而何也”?(二)孔子已被歷代封建統治者改鑄為專制君主的“護符”,成為保護君主政治的“偶象”,“故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象的權威”,“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⑾。(三)孔子學說自然不儘是封建性的糟粕:“孔子之說,今日有其真價,吾人亦絕不敢蔑視。”(四)如何繼承和發揚孔學中的“真價”?“惟取孔子之說以助益其自我之修養”,而不是“奉其自我以貢獻於孔子偶象之前”⑿。後來,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中,李大釗進一步結合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闡明了孔子學說在中國的歷史地位及其最後“歸於消滅”的歷史必然性。
從世界文化發展的總趨勢看來,李大釗認為,絕不是以中國儒學來統整世界文明,而必須是東西兩種文明各“以異派之所長補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煥揚光采、發育完成之一日”,也正是以俄羅斯文明為“媒介”的“第三新文明之崛起”。就是說,這種“第三新文明”乃是繼承了東西兩派文化互相“取長補短”的優秀成果的結晶。這個觀點,不只是有力地抨擊了復古派的謬論,就是在當時新文化界說來,也非同凡響!
(二)五四運動爆發了,中國“固有文明”受到猛烈衝擊,新文化運動更加深入人心,守舊派既不能正面詆毀新文化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運動的潮流,亦不便公開鼓吹類似“中體西用”的觀點,於是揭櫫“新舊調和”論的旗號。1919年11月章士釗在《東方雜誌》第16卷11號發表《新時代之青年》,則是有代表性的。他說:保存國粹固然不妥,抄拾歐化亦未必行當,正確的態度應是“一面開新”,“一面復舊”,“物質上開新之局,或急於復舊,而道德上復舊之必要,必甚於開新”,只有促使新舊調和,把東西文化“熔鑄一爐”,庶幾做到“國粹不滅,歐化亦成”。這種新舊折衷的議論,表面看來不偏不倚,實際上仍是要把西洋文明“融合於吾固有文明中”。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人物,不能不從理論上予以解剖。
陳獨秀對調和論明確表示反對。他認為新舊雜糅、調和、緩進,是客觀存在的自然現象,不是人們的主觀主張。從這一觀點出發,他認為“物質上應當開新,道德上應當復舊”的命題是錯誤的,因為包括西洋在內的一切不良社會現象都是舊道德造成的,都應革除。他有時甚至把西洋社會的舊道德同“私有制度”聯繫起來,接近於唯物史觀的論點。但在總體上他對舊道德的批判,主要是為了改造國民性。他把社會進步的基礎放在意識形態的思想改造上,而不是放在經濟基礎的改造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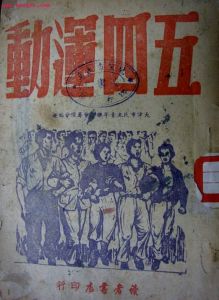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李大釗在“五四”以前也明確主張中西文化的調和,反對以一種文化征服另一種文化。但是,李大釗的調和中西文化的主張,與章士釗等人在文化方面的調和論是有本質區別的。章士釗認為,調和是“新舊雜糅”,是在保存舊的基礎上進行,結果是復舊;李大釗主張,新舊調和是“對抗”與統一併存,是在吸收新的基礎上進行的,其結果是“創新”。為了闡明他關於思想文化領域新舊調和、融會的主張,李大釗曾極力讚賞這樣形象的觀點:“孔子與牛肉,釋迦與雞肉,基督與蝦,乃至穆罕默德與蟹,其為吾人之資養品等也。吾人食牛肉、雞肉,在使之變為我之肉也。吃蝦蟹等物,在使之變為我之物也。”接著,他發表了《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等文,對於章士釗提出的“物質開新,道德復舊”的具體調和論,進行了有力的抨擊。他指出,道德是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人類社會包括道德在內的一切精神的構造都是表層構造,只有物質的經濟的構造才是這些表層構造的基礎構造。物質常有變動,精神構造也隨著變動,“物質既須急於開新,道德亦必跟著開新”,而“斷無單獨復舊的道理”,因為“物質與精神是一體的”。
李大釗初次用唯物史觀對封建舊道德的批判未免也有缺陷,如他講道德“是社會的本能”,而這種社會本能“也不是人類特有的,乃是動物界所同有的”等觀點,顯然包含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殘餘,但是從總體上看來,他對封建舊道德這一複雜問題的剖析,在當時新文化論壇上卻高人一籌,象陳獨秀、吳虞、魯迅等對封建舊道德都作了尖銳有力的批判,但都仍未能揭露封建道德和封建基礎的關係。李大釗對封建舊道德的解剖,也表明他基本完成了由進化論到唯物史觀的思想轉變,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三)五四運動過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浪潮日益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這樣東西文化的論爭又重新掀起一場“新舊思潮的大激戰”。
1920年春天開始,梁啓超發表了《歐遊心影錄》。他以自己經歷的見聞,說明西方文明已經“破產”,即是“頂時髦的社會主義,結果也不過是搶麵包吃”,還是要東方文明去“超拔”它。他原是西方文化的崇奉者,現在卻豎起反對西方文化的旗幟,同守舊派握手言歡。同年8月,梁漱溟在濟南作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講演,從文化淵源、人生哲學的角度對新文化運動進行了總清算。他得出結論說,人類文化要發生“由西洋態度變為中國態度”的“根本改革”,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之復興”。梁漱溟在新文化運動前期雖然不是擁護舊文化的主要代表,但在守舊派的主張被打得丟盔卸甲時,他自告奮勇起來應戰了。二梁的觀點在思想輿論界引起了極大的轟動,“東方文明”的擁護者的喧嚷一時甚囂塵上。
 梁漱溟
梁漱溟梁漱溟為了復興東方封建主義文化,不僅求助於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力論,把孔子描繪成為生命主義者,而且求助於羅素“衝動論”,說什麼“孔子是全力照注在人類情志方面……西洋人向不留意在此,現在留意到了,乃稍稍望見孔子之門矣!”很明顯,梁漱溟是在用西方帝國主義文化為中國封建主義文化作註腳。這實際上是傖父早在1917年提出的任務,現在由他來完成。鄧中夏說得好:“梁漱溟一系,底子上雖然是七分印度思想三分中國思想,面子卻說西洋思想亦有他的地位。”正因為如此,當時以梁啓超、梁漱溟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觀點,雖然也受到以胡適、吳稚輝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的批判,但論戰並沒有真正展開,雙方的勝負也不很明顯。1923年又發生較大規模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也稱“科學與玄學之爭”),雖然是哲學方面的爭論,就其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傾向來說,亦可視為東西文化論戰的繼續。如陳獨秀所說:這次論戰雙方的主要代表也只不過“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實質上是唯心主義營壘中的一場混戰。可見,這次東西文化論戰的後期,人們所關注的中心已不是原來意義上新舊文化的關係,而是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的關係,歷史重新提出了中國究竟向何處去的問題。
這時,矗立在新文化運動論壇的中流砥柱,是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人。李大釗所發表的一系列文章,雖然不象從前那樣以直接參加東西文化論戰的形式出現,但他所闡述的思想觀點,都是為了解答這一重大歷史課題的深刻見解,代表了馬克思主義者在文化戰線上的新成就和新水平。
早在1918年,李大釗在論述東西文明的差異時曾說:“東洋文明既衰頹於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於物質之下”,世界“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如果說那時還沒有看清楚這種既非封建主義又非資本主義的第三新文明是何性質的話,那么經過多年的東西文化的論爭,現在就可以得出“第三新文明”乃是社會主義文明的偉大結論了。他在20年代初期所發表的《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社會主義下之實業》、《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社會主義下的經濟組織》、《社會主義釋疑》等大量著述,正是這一偉大結論的科學闡釋。
 胡適
胡適在這一系列的文章中,他除了繼續駁斥各方面對西方輸入馬克思主義的種種誣衊和攻擊,如所謂“外來進口主義無用論”、“過激主義危險論”等等之外,主要就以下三方面論證了中國必行社會主義的問題:第一,從時代特點看,十月革命後世界已出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對立的體系,“中國人民在世界經濟上的地位,已立在這勞工運動日盛一日的風潮中,想行保護資本家的制度,無論理所不可,抑且勢所不能”。第二,從世界革命發展的進程看,“人家已經由自由競爭發達到必須社會主義共營地位,我們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發點,按人家的步數走,正如人家已達壯年,我們尚在幼稚;人家已走遠了幾千萬里,我們尚在初步。在這種勢力之下,要想存立,適應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併力社會共營的組織,不能有成“。就是說,要繞過資本主義階段,走向社會主義道路,“兼程併力”地前進。第三,從中國“發展實業”的需要看,他說:“用資本主義發展實業,還不如用社會主義為宜”。在“社會主義之下,資本可以集中,勞力可以普及”,“有此種資本與勞力,以開發公有土地之富源,那愁實業不突飛猛進”?同時,他還批判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並同種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劃清界限,堅持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如果說在“五四”以前,李大釗曾提出:“我總覺得布爾什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必須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產階級”,“在我們這不事生產的官僚強盜橫行的國家”,“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班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那末到現在,他已經開始探索把社會主義原理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具體道路。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李大釗這大量的思想觀點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著述在新文化論壇上的出現,標誌著近代中國古今中西的文化論戰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革命者開始向西方學習馬克思主義真理並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
(四)在“五四”東西文化論戰中,李大釗的中西文化觀具有哪些特點呢?
第一,在文化問題上,他採取具體分析的態度。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反過來又影響於一定社會的政治與經濟。李大釗在批判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讚揚社會主義文化時,並沒有忘記著眼於它所處的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狀況:既看到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曾經起過的進步作用,又揭示了它們當前的“窮弊”;既說明中國社會需要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緊迫性,又懂得這種學習的艱苦性,“不可不以強毅之氣力赴之”。在學習的問題上,既有批判,又有繼承和創新;等等。儘管他這樣做是有一個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經歷了由樸素辯證法到唯物辯證法的轉變,但從總體上看,同其他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相比,他注意力求避免和減少形上學和絕對化的毛病。
第二,李大釗重視對文化現象的歷史主義分析和階級分析的統一。例如,他認定孔子的學說在我國春秋時代“確足以代表其社會其時代之道德”,不愧為那個時期的“中樞”和“聖哲”;但是要看到孔學“對於勞動階級,總是把他們放在被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階級的犧牲,‘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可以代表孔門賤視勞工的心理”。人類歷史發展到了今天,無產階級所要提倡的是“大同的道德”,即共產主義道德。對資本主義文化的共和制、代議制的分析,都貫徹了這種歷史分析和階級分析的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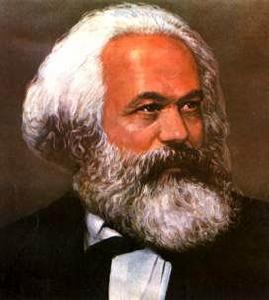 馬克思
馬克思第三,將文化作為社會現象來認識,十分注意文化的時代性和民族性問題。李大釗曾強調學習西方文化,需要從當前本土民族的特點出發,如說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雖已過時,但對於我們後進的民族,“則實居優越之域”,值得吸取。又如尼傑(Niet-zsche)的學說,“倡言超人哲學,鼓吹英雄主義,讚美力之享受,高唱人格之權威,宣傳戰爭之福音,而欲導現代文明於新理想主義之域”,這固然是由於帝國主義時代的哲學有它反動的一面,但是,從當時我國民族文化心理特點的需要看,又不無借鑑意義。因為“其說頗能起衰振敝,而於吾最拘形式,重因襲,囚錮於奴隸道德之國,尤足以鼓舞青年之精神,奮發國民之勇氣”。當然,這個意見的本身,也可深入探討,但他重視文化的時代性和民族性的統一,則是可取的。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偉大功績在於突出強調了文化的時代性,以及指出在文化心理方面應該樹立批判的精神,從而在中國歷史上呼喚出了一個新時代,但由於“五四”人物不注意文化還有民族性這一面,也就使運動存在重大缺陷。關於這一點,在李大釗的著作里似乎給予了必要的重視。
第四,歸根結蒂說來,李大釗在論戰中是把革命性和科學性相結合的。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隨著論戰的發展,守舊派勢力在不同的階段採用了不同的策略,迂迴作戰。但李大釗既英勇頑強,又機智靈活,不是處處同他們“短兵相接”,甚至運用了對方所提出的概念如“動”、“靜”、“調和”等,以發揮自己的思想,便於在思想體系上針鋒相對。他把這種鬥爭藝術完全置於科學基礎,即進化論和歷史唯物論之上,所以他能夠站到時代潮流的最前面,指導潮流前進。
在五四東西文化論戰中,由於李大釗的中西文化觀有上述一些特色,終於和其他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一起,把近代中國古今中西的文化論爭,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即革命者開始向西方學習馬克思主義真理並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以指導我國新文化建設的階段。
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長期以來是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思想,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我國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孕育和發展經歷了艱難曲折的過程。尤其是十年“文革”時期,由於極左路線的推行,一方面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封建毒素嗜痂若癖,另一方面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一概排斥,造成了文化思想的混亂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遲滯,經過多年的撥亂反正,才有所好轉。隨著改革開放總方針的執行,“全盤西化”和提倡中國“國粹”論的影響,在新的歷史時期又以不同的形式和在某種程度上開始滋生。可見如何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既大膽吸收東西方一切有價值的文化成果,又能防止和克服其消極因素,仍是一個有待進一步解決的重要課題。我們重溫李大釗的中西文化觀,在解決這一課題中,具有切近的參考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