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信息
| 書名: |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 | 頁數: | 536 |
副標題: | 出版社: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
作者: | [俄]娜傑日達·曼德施塔姆 著 劉文飛 譯 | 出版時間: | 2013-9 |
作者簡介
娜傑日達·曼德施塔姆(1899—1980) 俄羅斯著名詩人曼德爾施塔姆的妻子,作家,翻譯家。1899年10月30日生於薩拉托夫,娘家姓哈津娜。1919年5月1日與曼德施塔姆相識於基輔一家咖啡館,三年後二人結婚。經歷了二十年代中後期的短暫平靜之後,娜傑日達不得不面對丈夫的兩次被捕。這位被丈夫稱為“黑暗歲月的同志”的妻子,僅與丈夫共同生活了十六年,其中的最後四年還是在流放地度過的。六十年代初,娜傑日達開始撰寫關於丈夫、關於那個恐怖時代的回憶錄,即七十年代相繼成書的“回憶錄三部曲”《回憶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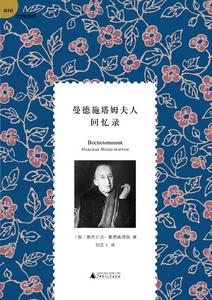
內容簡介
這兩本回憶錄當然是閱讀曼德施塔姆詩歌的指南,但是其意義不僅於此。任何一個詩人,無論他寫作了多少作品,從實際的或統計學的角度看,他在他的詩中所表現出的至多是他生活真實的十分之一。……奧西普·曼德施塔姆遺孀的回憶錄正好涵蓋了其餘的十分之九。這些回憶錄驅走了黑暗,填補了空白,矯正了誤解。其總體效果接近於一次復活逝者的行為,那害死詩人、比詩人存在得更久並仍繼續存在、更為普遍的一切,也在這些書頁中得到再現。由於這些材料的致命力量,詩人的遺孀在處理這些成分時如拆卸炸彈一般小心。由於這樣的精心,由於這部偉大的散文是用曼德施塔姆的詩歌、用他的死亡過程和他的生命質量寫成的,因此,一位哪怕沒有讀過曼德施塔姆任何一句詩的人也能立即明白,這些文字再現的確實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僅憑那朝向他的惡所具有的數量和能量。——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布羅茨基
編輯推薦
本書是俄國詩人奧西普·曼德施塔姆遺孀娜傑日達的回憶錄,這本回憶錄不僅是成熟的文學作品,還帶有深刻的政論性質,它對於蘇聯大清洗時代的社會眾生相的描繪窮形盡相,入木三分。詩人及其作品在那個時代的遭遇也令人唏噓。任何讀過這本書的作者都會感激娜傑日達的回憶和分析。全書有中譯者序、俄文版序以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布羅茨基的熱情推薦。圖書目錄
中譯本序/劉文飛1俄文版序/尼·潘琴科27
文明的兒子/約·布羅茨基47
娜傑日達·曼德施塔姆/約·布羅茨基63
五月之夜1
抄家5
晨思10
第二輪15
菜籃子19
門路21
社會輿論25
探監30
理論與實踐35
聚會和送別41
另一邊45
非理性48
同名人55
朱古力59
跳樓62
切爾登67
錯覺72
職業和疾病78
“裡面”83
赫里斯托夫雷奇89
誰之罪96
“副官”100
奇蹟之實質105
前往目的地109
別殺人114
俄國革命之女性122
傳送帶127
金翅雀的故鄉134
醫生和疾病139
委屈的房東144
錢153
奇蹟之源162
兩個截然相反的人167
兩種聲音173
毀滅之路176
投降182
價值重估190
勞作202
嚅動和絮語206
書和筆記本213
組詩216
雙重枝椏222
沃羅涅日的最後一冬229
頌詩234
金科玉律239
我的“希望”246
“附加的一天”251
比薩拉比亞馬車254
幻覺259
唯讀一本書的讀者264
科里亞·吉洪諾夫272
書架276
我們的文獻287
義大利290
社會結構297
不需要302
大地和塵世因素305
檔案和聲音313
舊與新323
警察維納斯328
偶然性332
電工337
別墅客341
狼飽肚子靠腿勤346
晚會和奶牛350
老友354
非黨的塔尼婭358
詩歌愛好者365
暗淡371
日常生活一幕375
自殺者379
新生活的使者383
最後的牧歌389
紡織工人396
什克洛夫斯基一家401
馬里納小樹林405
同謀408
媽媽送小姐來薩馬基哈療養413
五一節416
古戈夫娜420
陷阱424
索菲伊卡的小視窗427
死亡日期433
還有一個故事448
書摘隨讀
五月之夜抽了阿列克賽·托爾斯泰阿·托爾斯泰(1882—1945),作家。一個耳光後,奧·曼立馬返回莫斯科,然後每天給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打電話,央求她趕到莫斯科來。她遲疑不決,他生了氣。她已經打算去買車票了,卻仍站在窗前思忖。“您是在祈禱您自己別遇到這種厄運吧?”普寧普寧(1888—1953),藝術學家,1923年與阿赫馬托娃結婚,多次被捕,死於獄中。問道,他是一個聰明熱情、十分出色的男人。就是他,一次與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在特列季亞科夫畫廊轉悠時突然說了一句:“現在我們去看看您將來怎么上絞架吧。”於是便有了這樣的詩句:“往後,靈車將在黃昏碾過髒雪……哪位瘋狂的蘇里科夫將描繪我的結局?”這兩句詩引自阿赫馬托娃1939年所作《我知道,原地不動……》一詩。但她最終並未踏上這樣的旅途。“他們最終會揪住您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普寧常說,每當此時,他臉上便會掠過一陣抽搐。但是,他們最終忘記了她,並未抓她,相反,是她送包括普寧在內的許多友人踏上了最後的路途。
去車站迎接安娜·阿赫馬托娃的是廖瓦即列夫·古米廖夫(1912—1992),阿赫馬托娃和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所生之子,歷史學家,多次被捕入獄。,他當時住在我們家。我們把這件並不複雜的事情託付給他是個錯誤,他自然要設法錯過母親,她很是生氣,臉色不同以往。那一年,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常來我們家,她早已習慣在車站就聽到曼德施塔姆講的最新笑話。她還記得,一次列車晚點,曼德施塔姆說了這么一句動氣的話:“您是以安娜·卡列尼娜的速度趕來的。”又一次,列寧格勒下雨,她身著雨靴和帶風帽的膠皮雨衣,莫斯科卻艷陽高照,於是曼德施塔姆說:“您幹嗎打扮得像個潛水員似的?”他倆每次見面都滿心歡喜,無憂無慮,就像當年在詩人行會1911—1914年存在於彼得堡的詩人團體,參加者有古米廖夫、戈羅傑茨基、阿赫馬托娃、曼德施塔姆、洛津斯基等,他們構成阿克梅詩派的中堅。碰面的那個男孩和那個女孩。“得了,”我常常高喊,“我可無法和你們這兩隻鸚鵡生活在一起!”但是這一回,在一九三四年五月,他倆卻高興不起來了。
這一天十分漫長。翻譯家大衛·勃羅茨基大衛·勃羅茨基(1895—1966),詩歌譯者。傍晚過來,他屁股坐得很穩,幾乎無法讓他挪動地方。家裡一無所有,什麼吃的也沒有。奧·曼去鄰居家,想找點東西給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當晚餐……勃羅茨基跟著他衝出門去,我們指望勃羅茨基在失去男主人公的關照後會感到無聊,轉而離去。奧·曼很快就回來了,帶著一份收穫,即一枚雞蛋,可是他仍舊未能擺脫勃羅茨基。勃羅茨基重新坐進扶手椅,繼續清點他喜愛的詩句,這些詩句出自他喜愛的兩位詩人,即斯盧切夫斯基斯盧切夫斯基(1837—1904),詩人。和波隆斯基波隆斯基(1819—1898),詩人。,他對我們俄國的詩歌和法國詩歌均了如指掌。他就這樣坐著,不住地引用詩句,不住地回憶往事,直到午夜過後我們才明白他如此死乞白賴留在這裡的原委。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來我們家時就住在小廚房裡,煤氣還沒通,所謂的午飯我通常就在過道里用煤油爐做,出於對客人的尊敬,毫無用處的煤氣灶被蓋上一張油布,搖身一變為一張桌子。這廚房被稱為神廟。“您幹嗎像個神像似的待在這神廟裡?”納爾布特納爾布特(1888—1938),詩人,“詩人行會”成員,死於集中營。有一次看了一眼廚房裡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問道,“最好到哪個座談會上去坐一坐……”廚房就這樣成了神廟,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坐在廚房裡,讓奧·曼孤身一人遭受詩歌愛好者勃羅茨基的折磨。半夜一點左右,突然響起一陣聲音清晰、意味深長的敲門聲。“是來抓奧夏的。”我說了一句,過去開門。
門外站著幾個男人,我覺得他們人數很多,他們全都著便裝。我腦中霎那間閃過一個念頭,希望他們不是來抓人的,因為我一時還未注意到被風衣罩住的軍裝。實際上,這種風衣也是軍裝,就像沙皇密探的那身灰黃色便服,不過我當時對此並不知情。
不速之客剛邁過門檻,我的希望便立即煙消雲散。
我希望照例聽到:“您好!”或者:“這是曼德施塔姆家嗎?”或者:“家裡有人嗎?”最後,或者是:“請接收電報……”要知道,造訪者通常會與開門者打聲招呼,等待開門者把他讓進屋去。可我們時代的這些夜間造訪者們,卻不遵從古往今來世界各地每個秘密警察興許都會遵從的儀式。他們什麼話也不問,也不等主人開口,不在門前有片刻遲疑,便動作不大地推開我,身手敏捷地走進前廳,房間裡立馬擠滿了人。他們已經開始檢查證件,並動作相當熟練、準確、得體地摸索我們的腰間和口袋,看是否藏有武器。
奧·曼從大房間走出來:“你們找我?”他問道。一位身材不高的特工幾乎面帶微笑地看了他一眼:“您的證件。”奧·曼從口袋掏出護照。
那位契卡契卡起初為“肅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設委員會”之簡稱,後成為秘密警察機構的代名詞。人員看了看證件,向奧·曼出示傳票。奧·曼讀了傳票,點點頭。
用他們的語言來說,這叫“夜間行動”。正像我後來獲悉的那樣,他們每個人都堅信,在每一個夜晚,在我們這樣的每一個家庭,他們都有可能遭遇抵抗。為了鼓舞士氣,他們那個圈子裡流傳著許多關於夜間危險的浪漫傳說。我本人曾聽說一個故事,說巴別爾巴別爾(1894—1940),作家,後被判槍決。就曾開槍,重傷一名“我們的人”,講這故事的人是一位契卡高官的女兒,她父親在一九三七年得到高升。對於她來說,這些傳說與為上“夜班”的父親擔驚受怕的心情密切相關,她父親和藹善良,非常喜愛孩子和動物,在家時總是抱只小貓在腿上,但他教導他女兒永遠不要承認自己有錯,對任何問題都要堅決說“不”。這位懷抱小貓的和善之人,卻斷不會替那些被迫承認各種指控的被調查者開脫。“他們幹嗎要這么乾呢?”女兒常學著父親的樣子說道,“要知道,他們這么乾,結果讓他們自己和我們都陷了進去!……”“我們”,也就是那些帶著傳票在夜間造訪的人,就是那些進行審訊和作出判決的人,他們同時也會在閒暇時分將關於夜間險情的有趣故事講給朋友們聽。這些關於夜間激情的契卡傳說時常讓我想起巴別爾腦門上的那個小窟窿,這個小心翼翼、腦門高聳的聰明人,一生中或許從未舉起過手槍。
他們走進我們安寧的、家徒四壁的家,就像走進強盜老巢,走進賊窩,走進秘密實驗室,在這裡,頭戴面具的秘密分子正在準備炸藥,打算展開武裝抵抗。他們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三至十四日夜間闖入了我們家。
他們檢查了證件,出示了傳票,並確信不會有抵抗,然後開始搜查。勃羅茨基憂鬱地陷在扶手椅里,一動也不動。他身材巨大,就像某個野蠻民族的一尊木頭雕像,他坐在那裡呼哧著,他呼哧著坐在那裡。他神情兇狠,怒氣沖沖。我很偶然地求他幫個忙,好像是讓他在書架上找本書給奧·曼,他卻搶白道:“讓曼德施塔姆自己來找。”然後便又呼哧起來。天快亮時,我們已經能在兩個房間裡自由走動,疲憊不堪的契卡人員甚至不再緊盯著我們,勃羅茨基突然緩過神來,像小學生一樣舉起手來,請求準許他去趟洗手間。負責搜查工作的官員面帶嘲諷地看了他一眼,說道:“您可以回家了。”“什麼?”勃羅茨基驚訝地反問一句。“回家去吧。”契卡人員重複了一句,轉過身去。軍官們都很蔑視他們的平民幫手,勃羅茨基或許就是被他們安排到我們家裡來的,好讓我們在聽到敲門聲後來不及銷毀某些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