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23~1696年
《清史稿》卷二百七十八 列傳六十五
慕天顏 阿山 噶禮
慕天顏,字拱極,甘肅靜寧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授浙江錢塘知縣。遷廣西南寧同知,再遷福建興化知府。康熙九年,擢湖廣上荊南道。總督劉兆麒疏言天顏習邊海諸事,請調福建興泉道。尋擢江蘇布政使。十二年,喪母。總督麻勒吉、巡撫瑪祜疏言:“天顏廉明勤敏,清積年逋賦,厘剔挪移,事未竟,請令在官守制。”十三年,入覲,疏言:“江南田地錢糧有隱佔、詭寄諸弊,臣飭州縣通計田額,均分里甲;又因科則不等,立徵收截票之法,每戶實征錢糧分十限,於開徵日給限票,依限完納截票。逾限未截,按數追比,吏不能欺民。”下部,著為令。
十五年,擢江寧巡撫。疏進錢糧交代冊,上嘉其清晰,命布政使交代當以此為式。尋以節減驛站錢糧,加兵部侍郎。師征吳三桂,大將軍貝勒尚善請造船濟師,下天顏督造送岳州。敘勞,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仍兼右副都御史。時諸道兵應徵發,舳艫蔽江,夫役牽挽,動以千萬計。天顏疏言:“縴夫募諸民間,夫給銀一錢。民爭逃匿,計里均派,先期拘集,饑寒踣頓。及兵既到,計船給夫,兵與船戶橫索財物,鞭撻死傷。臣擬軍赴前敵,仍給縴夫;其凱鏇還京,並各省調遣歸標官兵,每船應夫若干,以其直給船戶,令雇水手。”上從之,命下直省,著為令。
江南水道交錯,天顏為布政使時,請於巡撫瑪祜,濬吳淞江、劉河淤道。十九年,江南困霪雨,疏言:“附近吳淞江、劉河諸州縣水道通暢,鏇溢鏇消。宜興、常熟、武進、江陰、金壇諸縣水無出路,或要口湮塞,致積雨成壑。常熟白茆港為長洲、崑山、無錫諸水出海要道,武進孟瀆河為丹陽、宜興、金壇諸水歸江要道,請動帑疏濬。”上從之。於是濬白茆港四十三里達海,濬孟瀆河四十八里達江,皆建閘以時啟閉,費帑九萬有奇。又嘗疏請減浮糧,除版荒、坍沒公占田地,部議坍沒許豁除,版荒令復勘。二十年,疏請募民墾版荒,六年後起科。
揚州知府高德貴虧帑數萬,既劾罷,鏇卒;天顏疏銷草豆價,戶部覈減七千有奇,天顏檄追德貴家屬。京口防禦高騰龍,德貴族也,與參領馬崇駿以天顏奏銷浮冒訐於將軍楊鳳翔,鳳翔格不行。總督阿席熙劾崇駿、騰龍婪取,上遣郎中圖爾宸、鍾有德會天顏勘治。崇駿、騰龍叩閽訟天顏奏銷浮冒,惡其訐告構罪狀,唆總督劾奏。上命圖爾宸、鍾有德具獄,崇駿、騰龍婪取罪至死,天顏以草豆價戶部覈減諉罪德貴,當左遷。得旨,如議。
天顏將去官,疏列成勞,且言:“夙夜冰兢精白,不意遭誣訐,蒙鑒宥不加嚴譴。”上以天顏未聞有廉名,乃自言“冰兢精白”,非是,命嚴飭。二十三年,起湖北巡撫,復諭之曰:“爾前為巡撫,未能潔己率屬。今宜痛改前非,廉謹自持,以副任使。”鏇移貴州。
二十六年,授漕運總督,疏言:“京口至瓜洲,漕船往來,風濤最險。請仿民間渡生船,官設十船,導引護防。”部議非例,不允。上曰:“朕南巡見京口、瓜洲往來人眾,備船過渡,有益於民。其如所請行。”天顏疏陳江南、江西累年未完漕項銀米請恩貰,上命盡免康熙十七年以前積逋。江南揚州、淮安所屬運河東瀕海諸州縣地卑下,謂之下河,頻歲被水。上先用湯斌議,遣侍郎孫在豐疏濬下河。河道總督靳輔議起翟家壩迄高家堰築重堤,束堤堰溢出之水北出清口,謂疏濬無益。天顏仍主疏濬,並修築高家堰,與不協。上遣尚書佛倫、熊一瀟,給事中達奇納、趙吉士會勘,佛倫等主用輔議,天顏、在豐議與輔異。天顏密疏力爭,輔疏劾天顏與在豐有連,欲在豐建功,故堅阻上游築堤。下部議,奪天顏職,而輔亦為御史郭琇、陸祖修,給事中劉楷交章劾罷。初,輔請於仲家莊建閘,引駱馬湖水,別鑿中河,俾漕船避黃河之險,天顏亦議為無益。上命學士開音布、侍衛馬武往視,還奏天顏令漕船毋入中河,上以責天顏,逮下獄。天顏反覆申辨,副都御史噶爾圖舉天顏訴辭先後互異,坐奏事上書不以實論罪,上追錄天顏造舟濟師,特寬之。三十五年,卒。
天顏歷官有惠績,嘗疏請有司虧帑雖逾限,於發遣前清償,仍貰其罪。獄囚因逸犯株連,待質已三年者,於秋審時開釋;獄囚無親屬饋食,月給米三斗:皆恤下之政。在江南,興水利,蠲積逋,而請免縴夫,甦一時之困,江南民尤頌之。獨劾嘉定知縣陸隴其不協於輿論,左都御史魏象樞疏言:“天顏劾隴其,稱其操守絕一塵,德有餘而才不足。今之有司,惟操守為難;既知之矣,何不留以長養百姓?請嚴飭諸督撫大破積習,勿使廉吏灰心,貪風日長。”會詔舉清廉,象樞遂以隴其應,語具隴其傳。
阿山,伊拉哩氏,滿洲鑲藍旗人。初自吏部筆帖式歷刑部主事、戶部員外部。康熙十八年,授翰林院侍講,七遷至戶部侍郎。三十年,命治賑西安、鳳翔二府,明年還京。上聞流民有至襄陽者,以問阿山。阿山言正月已得雪,民無流亡。上曰:“正月雖雪,二、三月雨不時,麥收未可望。流民至襄陽甚多,汝未之知耳。”坐奉使不盡心,左授郎中。三十三年,擢左副都御史。三十五年,上親征噶爾丹,阿山從。授阿密達為將軍,逐噶爾丹,阿山為參贊。師還,授盛京禮部侍郎。三十六年,授翰林院掌院學士。
三十九年,授江南江西總督。安徽布政使張四教以憂去官,巡撫高永爵劾四教擅動庫帑,下阿山察奏。阿山言四教動庫帑為公用,請免議,上復命具實狀以聞。阿山乃言:“三十八年上南巡,四教發庫帑十一萬供辦,議令各官扣俸抵補。各官皆自承,臣不敢隱。”上責阿山徇情沽譽,命漕運總督桑額鞫四教,論如律。阿山當奪職,上寬之,命留任。
四十三年,阿山劾江西巡撫張志棟大計不公,志棟及布政使李興祖、按察使劉廷璣、道員韓象起等皆奪職。阿山又言大計志棟主之,請復興祖等官。給事中許志進劾阿山恩威自擅,阿山疏辯,且詆志進為淮安漕標營卒子,素行不端,為志棟報復。志進亦追論阿山庇張四教,並收屬吏賄賂,盜倉谷不問,貪淫惡跡,縱妾父生事。疏並下部議,部議皆奪職。上復寬阿山,命留任如故。四十四年,疏劾江寧知府陳鵬年貪酷,並以妓樓改建講堂,凟聖諭,大不敬。命會桑額及河道總督張鵬翮集讞,坐鵬年罪至斬,上特命來京,事具鵬年傳。
阿山與桑額、鵬翮議自泗州開河築堤,引淮水至黃家堰,入張福口,會出清口,是為溜淮套,疏請上臨視。四十五年,授刑部尚書。四十六年,上南巡,臨視溜淮套,諭曰:“阿山等奏溜淮套別開一河,分泄淮水,繪圖進呈。朕策騎自清口至曹家廟,見地勢甚高,雖成河,不能直達清口,與所進圖不同。且所立標竿多在民冢上,朕何忍發此無限枯骨耶?”命鵬翮罷其事。下九卿議,阿山及桑額、鵬翮皆奪職;上以阿山主其議,命但坐阿山,遂奪職。五十一年,江蘇布政使宜思恭以虧帑坐譴,因列訴總督噶禮等頻向需索,阿山亦受節餽,下部議,上以阿山老,寬之。五十二年,萬壽,復原品。逾年,卒。
阿山故精察,上嘗問大學士李光地:“阿山在官何若?”光地奏:“臣嘗與同僚,廉乾,果於任事。其失民心,獨劾陳鵬年一事耳。”上頷之。
噶禮,棟鄂氏,滿洲正紅旗人,何和哩四世孫也。自蔭生授吏部主事,再遷郎中。康熙三十五年,上親征噶爾丹,次克魯倫河。噶禮從左都御史于成龍督運中路兵糧,首達行在,召對,當上意。尋擢盛京戶部理事官。歲餘三遷,授內閣學士。三十八年,授山西巡撫。噶禮當官勤敏能治事,然貪甚,縱吏虐民。撫山西數年,山西民不能堪。會潞安知府缺員,噶禮疏薦霍州知州李紹祖,紹祖使酒自刎,噶禮匿不以奏。上聞之,下九卿議罪,擬奪噶禮職,上寬之。御史劉若鼐疏論噶禮貪,得贓無慮數十萬,太原知府趙鳳詔為其腹心,專用酷刑以濟貪壑事。下噶禮復奏,得辨釋。
平遙民郭明奇等以噶禮庇貪婪知縣王綬,走京師詣巡城御史袁橋列訴。橋疏聞,並言“噶禮通省錢糧加火耗十之二,分補大同、臨汾等縣虧帑,餘並以入己,得四十餘萬;指修解州祠宇,用巡撫印簿勒捐;令家伶赴平陽、汾州、潞安三府迫富民饋遺;又以訟得臨汾、介休富民亢時鼎、梁湄金;縱汾州同知馬遴;庇洪洞知縣杜連登,皆貪吏;隱平定雹災”,凡七事。上命噶禮復奏,山西學政鄒士聰代太原士民疏留噶禮。御史蔡珍疏劾士璁“職在衡文,乃與巡撫朋比。且袁橋疏得旨二日後,太原士民即具呈,顯為誣偽。噶禮與士璁同城,委為不知,是昏憒也;知而不阻,是幸恩也。請並敕部議處”。尋噶禮復奏,以明奇等屢坐事走京師誣告,並辨橋、珍所言皆無據。下九卿察奏,明奇等下刑部治罪,橋、珍坐誣譴罷。
四十八年,遷戶部侍郎,鏇擢江南江西總督。噶禮至江南,益恣肆,累疏劾江蘇巡撫於準、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漢,皆坐罷。知府陳鵬年初為總督阿山劾罷,上復命守蘇州;及宜思恭罷,署布政使。鵬年素伉直,忤噶禮。噶禮續劾宜思恭虧帑,又論糧道賈朴建關開河皆有所侵蝕,遂及鵬年覈報不實,鵬年復坐罷。噶禮復密疏鵬年虎丘詩怨望,上不為動。
巡撫張伯行有廉聲,至則又與噶禮忤。五十年,伯行疏言本科江南鄉試取士不協輿論,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亦檢舉同考官知縣王曰俞、方名所薦士有不通文字者。上命尚書張鵬翮如揚州會噶禮及伯行察審。鵬翮至,會讞,既得副考官編修趙晉及曰俞、名諸交通狀,伯行欲窮其獄。噶禮盛怒,刑證人,遂罷讞。伯行乃劾噶禮,謂輿論盛傳總督與監臨提調交通鬻舉人;及事發,又傳總督索銀五十萬,許不竟其事:請敕解任就讞。噶禮亦劾伯行,謂:“方會讞時,臣正鞫囚,伯行謂臣言不當,臣恐爭論失體,緘口結舌。伯行遂陰謀誣陷,以鬻舉人得銀五十萬污臣,臣不能與俱生。”因及伯行專事著書,猜忌糊塗,不能清理案牘。時方有戴名世之獄,又言:“南山集刻板在蘇州印行,伯行豈得不知?進士方苞以作序連坐,伯行夙與友,不肯捕治。”並羅列伯行不職數事。
疏入,上並命解任,令鵬翮會漕運總督赫壽察奏。獄具,晉、曰俞、名及所取士交通得賄,當科場舞弊律論罪;噶禮劾伯行不能清理案牘事實,餘皆督撫會銜題咨舊事,苞為伯行逮送刑部,南山集刻板在江寧,皆免議;伯行妄奏噶禮鬻舉人,當奪職。上切責鵬翮、赫壽瞻徇,又命尚書穆和倫、張廷樞復讞,仍如鵬翮等議。上諭曰:“噶禮才有餘,治事敏練,而性喜生事,屢疏劾伯行。朕以伯行操守為天下第一,手批不淮。此議是非顛倒!”下九卿、詹事、科道察奏,復諭曰:“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江南必受其朘削且半矣。即如陳鵬年稍有聲譽,噶禮欲害之,摘虎丘詩有悖謬語,朕閱其詩,初無他意。又劾中軍副將李麟騎射皆劣。麟比來迎駕,朕試以騎射,俱優。若令噶禮與較,定不能及。朕於是心疑噶禮矣。互劾之案,遣大臣往讞,為噶禮所制。爾等皆能體朕保全廉吏之心,使正人無所疑懼,則海宇蒙昇平之福矣。九卿等議噶禮與伯行同任封疆,互劾失大臣禮,皆奪職;上命留伯行任,噶禮如議奪職。
五十三年,噶禮母叩閽,言噶禮與弟色勒奇、子乾都置毒食物中謀弒母,噶禮妻以別戶子乾泰為子,縱令糾眾毀屋。下刑部鞫得實,擬噶禮當極刑,妻論絞,色勒奇、乾都皆斬,乾泰發黑龍江,家產沒入官。上令噶禮自盡,妻從死,餘如部議。
論曰:廉吏往往不獲於上,豈長官皆不肖,抑其強項固有所不可堪歟?隴其之廉,天顏知之而不能容。鵬年初扼於阿山,繼挫於噶禮,皆欲中以危法,抑又甚矣。伯行與噶禮互劾,再讞不得直。幸賴聖祖仁明,隴其復起,鵬年致大用,伯行亦終獲全。二三正人詘而得申,人心風氣震盪洋溢,所被至遠。噶禮不足以語此,蓋天顏、阿山亦弗能喻也
社會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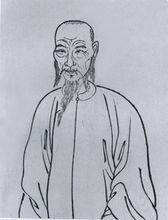 慕天顏像
慕天顏像慕天顏先祖為遼西鮮卑族人,複姓慕容,東晉鹹康三年(337),慕容氏先祖慕容皝建立
前燕政權。其後慕容族裔流散各地。明初,慕容氏後裔有到平涼為官,遂家靜寧。到慕天顏的父親慕忠以後,便改“慕容”複姓為“慕”。
天顏生性聰穎,自幼喜讀書,且過目能誦,少有大志,胸襟曠達。時靜寧發生大旱,饑荒之年,餓殍浮地,天顏對父說道:“我家藏谷數千石,倉滿屯盈,何不賑濟饑民?”父驚其少小年級,竟有如此胸襟,遂開倉取谷,以濟饑民。天顏15歲補州諸生,在學,天顏求知求學心裡得不到滿足,遂到城郊西岩寺山研讀佛教經典《大藏經》,苦讀經年。後又精讀《四書》,學問日進。順治三年(1646)天顏23歲鄉試中舉,順治十二年(1655)成進士。翌年由吏部派往浙江錢塘縣縣令。自此始便歷經漫長的仕宦生涯,正如他所說:“儒者之學,貴於有為,除大害,興大利,學者分內最切事”。蹬上仕途,便開始施展他兼濟天下的抱負。任錢塘縣令時,正當沿海用兵,準備收復台灣。民眾負擔過重,供應浩繁,加之吏役魚肉百姓,民不聊生。天顏上任,鼎力隔除積弊,減輕了百姓負擔。時大軍駐紮浙省,準備占用民房,天顏堅持應在江岸築營,不可占用民居。後皇帝詔諭:“兵以衛民,何得入城”。人皆服其見識。浙江省從明末來即有盜匪潛藏山中,劫掠兒童為票,勒索贖金,多年此風不息。錢塘有巨盜張八,家資巨大,地方官不能制,天顏設法擒殺,斬其首犯數十人,協從教育釋放,使四境得以安寧。天顏任錢塘縣令七年,興利除弊,民風大變。
故事軼事
康熙二年(1663)升河南開封府同知,未及到任,其父去世,歸家守喪,三年期滿,補廣西南寧府同知。任期內,凡全省重大刑獄案,督府盡交天顏辦理。天顏深入瘴癘之地親自調查,凡疑難案件,均得水落石出。在南寧任職八月升為福建興化府(今莆田縣)知府。到任後,在短時內審理了牽連全省數百人的百萬軍需這一重大積案,天顏因此聲振朝野。不久奉詔以兼理太常卿充正使的身份招徠台灣鄭經。鄭經繼父鄭成功掌管台灣後,妄圖獨立,天顏到台灣後,告其古今興亡之理,向背利害之由,勸其回歸祖國,鄭經拒不接受。天顏說:“天朝法網寬大,特命我來宣布德意,你能反正,不動用武力,是為保全台灣人民的生命財產,何去何從,你想一想,可不要做後悔的事情。”經不從,天顏嚴詞告經:“你父,祖父皆我中國之臣民,豈有中國臣民的子孫不隸我版籍者,天朝皇帝仁復萬方,不忍以中國臣民流於外化,我今來是招我中國臣民回歸祖國,不是招外國人和外國土地,這是理之必然,誰也抗拒不了”。天嚴的義正嚴詞,大義凜然震撼了台灣民眾。天顏對途經島嶼,扼塞險易具詳細觀察繪圖,入奏朝廷,並對兵力部署和進兵方略提出詳細建議,對康熙二十二年(1683)統一台灣起了重要作用。
主要為官經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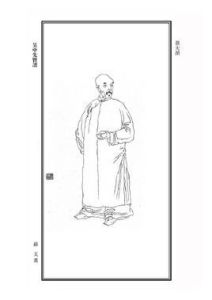 慕天顏紀念館
慕天顏紀念館康熙九年(1670)升湖廣上荊南道,因閩浙總督劉兆麒上奏云:慕天顏深諳邊疆海域政事,請調福建興泉道。還未曾赴任,恰遇江蘇布政使出缺,吏部循資以請,康熙以江蘇財賦重地,非賢能不足以當此重任。遂授天顏為江蘇布政使。上任時,前任移交全省財政庫銀一萬八千兩,任職後,正當用兵之際,開銷巨大,到離任時,庫存銀一百二十九萬七千多兩,項項清楚,款款分明。康熙嘉獎到:“蘇,松財賦浩繁,向來挪墊混淆,慕天顏任布政使後,實心任事,竭力清厘,有俾國計,朕甚嘉焉,據奏交代貯庫帑金豐裕,款項潔清,以後各布政使交代時,應照此式,詳明繕冊,具題爾部,一併定例議奏。”康熙十二年(1673)天顏表母。總督麻勒吉,巡撫瑪祜上疏言:“天顏廉明勤敏,清積年逋賦,厘剔挪移,事未竟,請令在官守制。”次年覲見康熙皇帝,陳言江南田賦徵收諸弊端,提出“吏不能欺民。”康熙十五年(1676)天顏擢任江蘇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不久因節減驛站錢糧,加授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是時,南寧靖寇大將軍勒爾錦正與吳三桂叛軍作戰,吳三桂固守岳州恃洞庭之險,清軍不能南下,雙方相持數年。繼而尚之信叛清,形勢更加險惡,康熙又派大將軍貝勒尚善分兵赴湖廣,尚善請造船濟師,康熙命天顏督造。不到四月全部竣工送往岳州,為岳州之戰的勝利作了貢獻。康熙降旨嘉獎,贊其“急公可嘉,勤勞茂著”。遂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銜,嗣後又晉升為光祿大夫。
江南水鄉,水道縱橫交錯,天顏為江蘇布政使時,請於巡撫,疏通吳淞江、瀏河淤道,使蘇、松、常、嘉、湖、杭六郡旱澇保收。康熙十九年(1680),江南霪雨,天顏請求撥款,又疏通了常熟白茆港45里,武進孟續河淤道48里,並制水閘旱蓄澇泄。他曾上疏請減浮糧,除版荒、坍沒、公占田地賦額。又親臨各地勘察,共察核出坍荒之地2306傾,歷年缺額銀230萬餘,奏請得以豁免。康熙二十年(1681),上書朝廷開放海禁,招募流民開墾版荒之地。同年,揚州知府高德貴虧缺庫銀數萬而被劾罷官,不久卒。天顏奏銷7000多兩,又檄追德貴家屬,以致被誣告,後訐告者雖被治罪,下獄至死,天顏亦被降職去官。二十三年(1684)春,復起任湖北巡撫,七月,調任貴州巡撫兼理湖北川東地方提督軍務。康熙二十六年(1687),任漕運總督。康熙皇帝將親政以來感到最棘手的三件事(三藩、河務、漕運)之一的漕運,委任天顏,足見康熙對天顏的賞識和重用。亦見天顏的辦事能力。天顏遂上疏:“京口至瓜州,漕船往來,風濤最險,請放民間渡生船,官設十船,導引護防。”部議未準,但康熙下旨:“朕南巡見京口,瓜州往來人眾,備船過渡,有益於民,如其所請行。”天顏復陳言,請免江南,江西累年未完成漕項額銀。
江南揚州淮安所屬運河東面瀕海各州縣,地勢較低,連年水患不斷,康熙納湯斌建議,遣侍郎孫在豐疏浚下游,河道總督靳輔認為疏浚無益,建議從翟家壩到高家堰築大堤,使運河水北出清口,天顏卻力主疏浚。天顏與孫在豐觀點同,並密疏力爭,靳輔亦上奏,謂天顏與在豐相連。雙方上疏爭辯。經詔勘察,部議後,天顏疏議未被採納,反而因此罷職。靳輔亦被交章劾罷。此前靳輔請在仲家莊建閘截水,引駱馬湖水,開鑿中河,俾漕船避黃河之險,天顏認為不可,故帝遣學士開音布,侍衛馬武往視,還朝奏說,天顏禁船入中河。天顏因此被捕下獄。康熙復念其昔日造船濟師之功,特予免釋,準其歸里。
天顏落職後,回歸故鄉靜寧,恰逢當地大旱,本人又疾病復發,遂帶家人到江南就醫。結果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四月十五日病逝於吳縣(今蘇州市)寓中,享年七十三歲。
康熙重臣--慕天顏
慕天顏在江南任官多年,頗多建樹,百姓交口稱讚,是靜寧歷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功臣。
金庸書中的慕天顏
慕天顏在《鹿鼎記》里出場不到80頁,但讀過這80頁,一個深諳官場處世之道、細心、乖巧、圓熟、周到、精幹的官僚形象如在眼前。欽差大臣韋小寶駕臨揚州,因故觸發了幼時所受的禪智寺和尚打罵之辱,不禁心頭火起,一心找茬想毀了禪智寺的芍藥盛景。“布政司慕天顏是個乖覺而有學識之人”(第1495頁),先順著欽差大臣的話說和尚的不是,接下來給欽差大臣講故事,說到後來,讓欽差大臣心滿意足:
慕天顏又道:“韓魏公後來帶兵,鎮守西疆。西夏人見了他怕得要死,不敢興兵犯界。西夏人當時怕了宋朝兩位大臣,一位就是韓魏公韓琦,另一位是范文正公范仲淹。當時有兩句話道:‘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將來韋大人帶兵鎮守西疆,那是‘軍中有一韋,西賊見之忙下跪’!”
韋小寶大樂,說道:“‘西賊’兩字妙得很,平西王這西……”忽然心想:“吳三桂還沒起兵造反,可不能叫他‘西賊’。”忙改口道:“平西王鎮守西疆,倒也太平無事,很有功勞。”吳之榮道:“平西王智勇雙全,勞苦功高,爵封親王,世子做了額駙。將來韋大人大富大貴,壽比南山,定然也跟平西王一般無異。”韋小寶心中大罵:“辣塊媽媽,你要我跟吳三桂這大漢奸一般無異。這老烏龜指日就要腦袋搬家,你叫我跟他一樣!”
慕天顏平日用心揣摩朝廷動向,日前見到邸報,皇上下了撤藩的旨意,便料到吳三桂要倒大霉,這時見韋小寶臉色略變,更是心中雪亮,說道:“韋大人是皇上親手提拔的大臣,乃是聖上心腹之寄,朝廷柱石,國家棟樑。平西王目前雖然官爵高,終究是不能跟韋大人比的。吳府尊這個比喻,有點不大對。韋大人祖上,唐朝的忠武王韋皋,曾大破吐蕃兵四十八萬,威震西陲。當年朱泚造反,派人邀韋忠武王一同起兵。忠武王對皇帝忠心不貳,哪肯做這等大逆不道之事?立刻將反賊的使者斬了,還發兵助朝廷打平反賊,立下大功。韋大人相貌堂堂,福氣之大,無與倫比,想必是韋忠武王傳下來的福澤。”
韋小寶微笑點頭。其實他連自己姓什麼也不知道,只因母親叫做韋春芳,就跟了娘姓。想不到姓韋的還有這樣一位大有來頭人物,這布政司硬說是自己的祖先,那是硬要往自己臉上貼金;聽他言中之意,居然揣摩到吳三桂要造反,這人的才智,也很了不起了。(第1498—1499頁)
話說到這個份上,“明知布政司轉彎抹角、大費心機的一番說話,意在保全這禪智寺前的數千株芍藥”(第1501頁),韋大人也得遵從官場規矩,不能駁了別人的面子。同樣是遵從官場的規矩,韋小寶“破獲”了“吳之榮策反案”後,慷慨地拉上撫台藩台,將這一大案“算是咱們三人一齊立的功勞好了”。這時候慕天顏說:“總督麻大人回去了江寧,欽差大臣回奏聖上之時,最好也請給麻大人說幾句好話。”(第1577頁)
這裡當然都是“小說家言”。但就慕天顏為官之謹慎周到,以及吳三桂叛亂前與慕天顏的關係而言,也有歷史真實的底色。《履園叢話·舊聞》“測字”條(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8頁):
閭門外上津橋朱某,家貧,欲入山尋死,遇仙解救,授測字一書,其驗如神。求之者必需預定日期,每日只測一字,取資一兩,懸牌門首,某日測某人字。時吳三桂將反,有文書來,向蘇藩庫借餉十萬兩。方伯慕公天顏躊躇莫決,乃延朱測字,且告以故。朱曰:“請命一字。”適几上有殘柬,慕公隨手翻轉,指“正”字為枚。朱曰:“不可借。‘正’似‘王’字,王心已亂。且柬正面合几上,正而反矣,即反之兆也。”慕即拒之。未幾,果應其言。
吳三桂沒借到的餉,當然用來打吳三桂了。《鹿鼎記》也有交代:
慕天顏又道:“皇上對吳逆用兵,可惜卑職是文官,沒本事上陣殺賊。卑職已秉承總督大人、撫台大人的意思,十天之內,派人押解一批糧餉送去湖南,聽由皇上使用。”(第1578頁)
相關科研資料
慕天顏
來源:《中國名人志 第十一卷》/清朝
| 編纂單位: | 中國名人志編纂委員會 |
| 編纂人員: | 澹泊 |
| 出版單位: | 中國檔案出版社 |
| ISBN: | 7-80166-145-1 |
| 出版時間: | 2001年12月 |
| 分類: | 地情概況->地方名人 |
| 頁數: | 2 |
| 條目類型: | 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