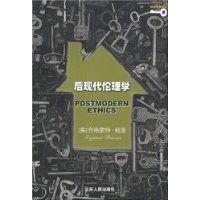書評
導言 現代和後現代透視下的道德
體現破碎存在者莫過於碎片。
——R·M·里爾克
正如題目所表明的那樣,本書是關於後現代倫理而不是關於後現代道德的研究。
如果要對後者(即後現代道德)進行研究的話,應該把目標定在對生活於後現代的人們所面對和努力去解決的道德問題進行一下可能的、全面的盤點。這些問題不但包括過去已經完全療治好而現在又以新形式出現的舊問題,也包括過去時代的人們不知道或沒有引起注意的新問題。兩種類型的問題都不少。我們時代的“道德議程”充滿了過去時代的倫理學家幾乎沒有或者根本沒有接觸到的題目,因為它們沒有被清楚地表達為人類經驗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只提及一下在夫妻關係、性別和家庭交往的現代困境中出現的多元的道德觀就足夠了,這些觀念因為它們習慣上的弱決定性、靈活性、易變性和軟弱性而臭名昭著。在多種多樣的傳統中,一些消失了,另外一些得到復興和重新發現後,為忠誠性和指導個人行動的權威性而相互競爭著。儘管建立一個令所有人都滿意的價值和觀念的等級制度是沒有希望的,但這種競爭將使人們從必須作出選擇的令人煩惱的任務中解脫出來。在另一方面,即在全球化語境的當代生活中,有的學者可能論及聞所未聞的、確確實實的災難性的危險,這些危險來源於部分和局部目標的相互交叉,它們不能被事先預測,即使行為以其被組織好的方式被安排時,這些危險也進入不了我們的視界。
在我的研究中,這樣的問題確實一次又一次地呈現,但是它們僅僅是作為背景出現的,在這種背景下,現代和後現代的倫理思想繼續發展著。這些問題被視為明確的後現代道德觀形成的經驗背景?從這種後現代倫理觀的角度進行思考時,這些問題呈現的形式及其被賦予的重要性正是本書的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主旨是後現代視角本身:本書的主要觀點是:當現代性到了自我批判、自我毀譽、自我拆除的階段時(在這個過程中,“後現代性”就意味著掌握和轉移),很多以前的倫理學理論(但不是現代的道德關懷)所遵循的路徑,開始看上去像一條盲目的小徑,同時,對道德現象進行激進、新穎理解的可能性之門被開啟了。
對後現代作品和當前關於現代性的作品熟悉的任何讀者都會注意到,關於倫理學上後現代“革命”的解釋是有爭議的,決不是只有一種可能性的解釋。現在的一些學者經常把對“倫理學之死”、倫理學的美學替代物和倫理學的最終解放等的頌揚與道德的後現代途徑聯繫起來。倫理學本身被誹謗或嘲弄為一種典型的、現在已被打碎的、注定要成為歷史垃圾的現代束縛,這種束縛曾經被認為是必需的,而現在被明確地認為是多餘的,也可以表達為另外_二個錯誤的觀念,即:後現代的人們沒有它也能生活得很好。如果有人需要一個對“後現代倫理革命”進行如此解釋的例子,他可以在吉里斯·里坡維特斯基最近出版的專著《責任的黃昏》(伽里瑪出版社,1992)中找到。作為一名卓越的“後現代解放”的吟遊詩人,《空虛時代》和《短命帝國》的作者,里坡導言現代和後現代透視下的道德維特斯基認為,我們已經最終進入了後義務論時代,在這個時代里,我們的行為已經從強制性的“無限責任”、“戒律”和“絕對義務”中解脫出來。在我們這個時代中,自我犧牲的觀念已經非法化了;沒有人被激勵或者願意使自己達到道德的最高目標,並去守護這種道德價值觀;政治家為烏托邦付出了代價,原來的理想主義者變得務實了。我們最普遍的口號就是:“不可越界!”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的時代,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僅僅被對寬容的需求所限制(當寬容與自我讚揚的和毫不猶豫的個人主義相結合時,可能僅僅表現為冷漠)。“後義務”的時代僅僅承認一種發育最不完全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根據里坡維特斯基的觀點,這是一種全新的情形,他勸告我們應去歡迎它的到來,並且對隨之而來的自由應感到欣喜。
里坡維特斯基犯了與許多後現代理論家相似的錯誤,即把研究的主題表述為研究的方法;把應當被解釋的東西用來解釋其他東西。描述普遍的行為並不意味著要作出道德上的陳述:這兩個程式在後現代正如它們在後現代以前一貫有差異的那樣是不同的。如果里坡維特斯基的描述是正確的,我們所面對的是一種從道德困擾中解脫出來的社會生活,抽象的“是”不再為“應該”所引導,社會交往已經從義務和責任中脫離出來,那么社會學家的任務就是發現道德規則如何從作為放置於社會自我複製的奮鬥的武器庫中退役的。如果社會學家恰好屬於社會思想中的批判潮流,他們的任務也.不僅僅停留在這一點。他們將拒絕接受“存在即合理”的觀念,也不會認為人類所做的僅僅是他們認為自己正在做的,或者是他們敘述自己所做過的。
本研究有一個假設就是:後現代道德的意義在於它給有批判意識的社會學家提供了繼續對上述問題進行比以前影響更大的調查的機會。
……
目錄
導言 現代和後現代透視下的道德
第一章 道德責任和倫理規則
第二章 難以捉摸的普遍性
第三章 難以捕捉的根基
第四章 兩類道德團體
第五章 道德團體之外
第六章 社會空間:認知的、美學的和道德的
第七章 私人道德、公共風險
第八章 結語:終點也是起點
注釋
譯者後記
等等
文摘
正是很好地表征了現代精神狀況的這種信念,在後現代階段被破壞並且被拋出流行的時尚(而與其一起的那些力量則由於它們的雄心仍然保持著活力)。對歷史景觀的後現代看法就是“全球化”的展望——信息、技術和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在全球範圍內傳播的景象,很明顯,不包括適合人類的政治、文化和道德權威(被認為要“全球化”的因素被看成是非國家的而不是國際的或者超國家的)。即便如此,這種新的歷史景觀放棄了通過遙遠的、灰暗的“文明進程”來達到道德普遍性的前景。
被剝奪了過去在“文化上先進”或者“最發達的”民族國家的“教化使命”中的基礎後,如果要生存下去的話,普遍道德的觀念只有返回到人類所共有的先天的、前社會的道德衝動(與社會進程的結果或者立法/命令/教育的最終結果和沉澱相對立),或者返回到人類平等的、共同的、最初的結構,它們同樣在時間上都領先於所有的社會衝突(見下一章)。這個可替代物將在戰場上讓步於普遍主義傳教士的永恆對手:共產主義的提倡者。一旦接受了這種可能性,即道德/文化主權的多元狀態(與政治/經濟主權的多元狀態截然不同)將要持續的時間不能確定,也許是永遠存在,我們就會發現我們正在從普遍道德價值冰冷、抽象的領域退入極有誘惑力的“土著公社”的舒適的、家庭般的庇護所;很多人會發現這種誘惑是不可抗拒的。因此人類世界“第一公社,的圖景現在開始得到強有力的支持,它的出現近乎被提升為經典和人類科學的無與倫比的“好觀念”。“第一公社”的圖景在現代的大多數時期被流放到了很少有人光顧的哲學和政治學反思的邊緣,被輕蔑地拒斥為“保守的”、“懷舊的”或者“浪漫的”,被將自身標榜為“隨時代步伐前進”、科學的和“進步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所湮沒。
無根自我之返根與普遍主義守護者拒絕將其警惕性局限在沿著國境建立的檢查站中一樣,再生的共產主義提倡者幻想的問題在於:被置於一定情境中的自我拒絕僅僅扮演被限制在“真正共同體”(即被理論家們構想的共同體)的邊境守護者的角色。共同體的邊界比國界更加難於以一種明確的方式劃出,然而,這並不是主要的問題。如果共同體身份要靠對被置於該共同體中的自我控制之手來確定,因而要靠能在其中產生道德輿論的傳播來確定的話,那么共同體邊界(特別是指多民族國家實踐的封閉的、管轄的、不可滲透的邊界;在一種較溫和的意義上也指環繞在文化/道德上相似的人口組成的統一體周圍的外形上參差不齊的邊線)的觀念變得更加難以而且是不可能得到贊成了。
不存在一種能夠與國家範圍的或者國家認可的機構相比具有合法判決權力的共同權威。在缺乏這樣一種權威的情況下,能夠真正對他們的成員有任何程度持久影響的共同體似乎與其說是一種生活事實,不如說是一種方法上的假定。不論何時,當任何人從概念的相對安全領域退入對任何具體對象的描述時,他就會發現這些概念僅僅代表一種人們根據相反目的來行動的可改變的共同體,在這樣的共同體中,充滿了內部爭論,明顯地缺乏在相互衝突的倫理命題之間作出公斷之手段。道德共同體被證明並不像假定的那樣空想,而且這種假定也是有爭議的。它經常是設定一種假定反對其他假定的問題;一個程式,一種束縛將來而不是保衛或者維護過去的願望;這種願望首先是一種把一定數量的人結合在一起的願望,使他們的行為服從於一定的選擇,這些選擇由於使共同體假定存在邊界的現實的努力而變得更加可取。在道德共同體中被描述為“道德的”正是這種服從希望達到的後果——對個體選擇的限制和改造是通過為了使這種團體真實存在而必須協作的需要達到的,這種需求被打扮成為了保持團體繼續存在的需要(這種需要經常以愚鈍和欺騙的方式被表達為為了全體利益[經常是假定的]而犧牲個體的、自身的利益之需要)。
當前國家在道德立法上的退出(或者更合適一點,放棄早期使這種立法成為全面普遍的現代雄心)使得公眾對這個領域進行自由管理。逐漸地,國家認識到小於民族的單位(以種族、領土、宗教、性別政策為基礎的)對道德指定和自我決定的權力——或者,更準確一些,它由於疏怠責任而不是由於蓄意設計允許了這種自我決定的發生。這種空虛現在由互相競爭的壓力填充,它們都要求著對來源於“被置於一定情境中的”自我的規則進行解釋之權利——正如它們所聲稱的,這是它們倫理監督的“自然”領域。一方面,“人權”是國家對其立法特權和其普遍深入的、愛挑剔的規範個體生活的過去雄心的退出——即國家在其範圍內甘心接受多樣性的永久存在,另一方面,在希望撿起國家放棄的權利的熱情的“共同體領導者”手中,“人權”變成了戰爭吶喊和勒索的武器。一方面,存在著對個性差異和新的道德自治的表達;另一方面,存在著儘管虛偽但卻堅決地使差異重新共同化和設計一種新的他治的努力——儘管這些都是在一個與前不同的水準上進行的。
過去所面對的是由國家限定和加強的法律/道德“普遍性”的濃縮權力,現在的個體被暴露於由各種社會壓力或者準倫理勒索狀態混合的雜音中,它們都試圖剝奪個體進行道德選擇之權力。然而,所有相互對立的壓力都不呼籲一種像以前的公民(國家的主體)一樣全面的情形。通常,綜合的“人類目標”削弱為一個面,就像撿起一塊石頭,在其上面將建立起假定中的共同體;個體的多面特性在此僅僅有一面被提出。然而,這一面被宣布對於在整體上決定個體的位置是關鍵的,這一面注定要使所有其他方面變得矮小,注定要超過所有其他方面——因此,預先免除了個體對將來可能加給他們的壓力進行的一切反抗。需要一種忠誠,這種忠誠應當使位於多面特性中其他方面的要求順從自己的相互競爭的要求變得次要、無效和空虛。為了真正變成“境遇自我”(situatedness),自我首先需要被修剪、整理、分割,然後重新組建。境遇自我(the situated self)的理論和服務於這個理論反映和支援的共同體建構的意識形態顛倒了這個過程的真正邏輯。遠非“自然給予”,“境遇自我”是在社會中、在爭論中產生的;它經常是一種相互競爭的鬥爭結果——時常是一種個體選擇。
通過國家立法之道德和被假定的共同體自我約定的代言人所散播的道德壓力在一點上是一致的:它們都拒絕或者至少剝奪了個體之道德判斷力。
它們都努力用他治的倫理責任來代替自治的道德責任。它們都想剝奪個體進行道德選擇的權利;或者至少在被認為與“共同福利”有關的生活領域剝奪個體實踐自由選擇的權利:萬一發生衝突,它們希望個體選擇能夠促進共同事業的行為——最重要的考慮(“全體利益高於個體利益”)。它們都對個體的主動權保持著警惕。它們都對在自發的、未預謀的、無管轄的交往過程中圍繞以自己為中心的友誼和忠誠具有厭惡感。它們都用懷疑的眼光看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網,認為它是反抗和煽動性言論滋生的沃土——等待有機會將它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