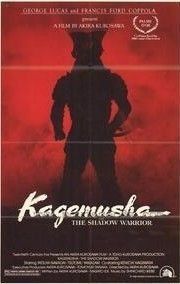故事梗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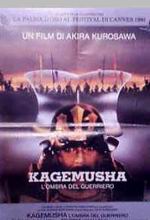 《影武者》
《影武者》《影武者》中的故事是發生在日本戰國時代武田家的事。武田家由武田信玄而興起,也最終因武田信玄的死而沒落。故事開始於武田家與織田、德川聯軍作戰時,武田信玄急死於軍中。一時間戰爭形勢急轉直下,先前優勢的武田軍忽然面臨著家族分裂,軍心大亂的危機。在危難關頭,幾個家臣秘密找出一名面容酷似武田信玄的盜賊假裝信玄以穩定軍心,順利退兵,並震懾住虎視眈眈的織田、德川、上杉、北條等豪強大名。按日本戰國的習慣,這個模仿者被稱為影武者。這樣的狀況維持了三年(影片中是三年)之久。三年之後影子武士的事,首先在家族中被揭露出來,引發了信玄之子武田勝賴全面奪取家中軍政大權,成為當主;並違背信玄遺訓領兵出征。結果被織田信長以三段式鐵炮射擊加馬柵欄戰術擊潰,全軍復沒。武田家精銳付之一炬,從此沒落。
經典場景
序幕,小全景,三個穿著一樣、長相相近的男人坐在各自的位置上,居中者是戰國三雄之首的武田信玄,左側是他的弟弟,右側前景,則是他弟弟剛剛從死刑場物色來做哥哥替身的影武者。黑澤明用一個長達6分多鐘的長鏡頭,一氣呵成地將三個人的背景、關係以及各自的鮮明性格展現得淋漓盡致。
天正元年,武田信玄攻打德川軍的野田城,月夜,他在圍城外聆聽城內的笛聲,受狙擊而負重傷。為穩定軍心,他留下遺言,命三年內嚴守他已不在人世的真相,而後歸天。身為竊賊的影武者肩負起扮演武田主公的重任,他從斷然拒絕到主動請命,從嘻笑無形到如主公附身,他令武田家人及敵手堅信他就是武田信玄,幫助武田軍闖過道道難關,然而,三年將至,信玄死去的訊息終被曝光,影武者也從氣勢如虹的主公瞬間淪為被放逐的一介草民。
文化解讀
歷史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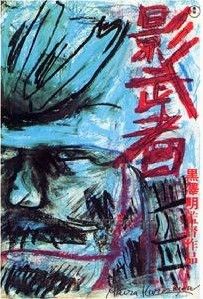 海報
海報話說永祿年間,天下大亂,群雄割據,各地大名厲兵秣馬,一路狼煙殺向京都,欲借朝廷和幕府之威名,行號令諸侯之陰謀。尾張(現日本愛知縣)大名織田信長先發制人,殲滅鄰國的今川氏和齋藤氏,將城堡遷往歧阜市。然今川氏所據之地卻為甲斐的武田信玄與三河的德川家康所瓜分。織田氏與德川氏結為盟軍,其勢驕人,然其敵手武田氏卻也掌握著日本史上最勇猛強大的軍隊——風、火、林三軍。於是,一場激烈的戰爭便在這個島國之上展開了——如果讓一位平庸的導演來演繹日本永祿、天正年間的這段歷史,極有可能被庸俗的鋪張成上述蒼白而陳舊故事——不論是傳奇,還是話本,或者是演義,都象是在唾沫與果皮橫飛的茶館中,一群無聊閒人的談資。幸運的是這個偉大的說書人是黑澤明。
武田信玄一心想進駐東京,一統天下。為了實現這個讓他狂熱無比的目標,武田信玄不惜成為一個極端冰冷的人。他殺死了自己的父親,放逐了自己的兒子,都是為了能夠讓自己的旗幟能夠飄揚在京都的上空。武田信玄在他圖謀天下的棋盤上遇到了織田信長和德川家康的聯軍。在征戰途中,他被對方手下的一個無名小卒用火槍擊傷,不治而亡。武田信玄在臨死前所看見的京都,在此時已為織田氏所據——天正元年(1573年),織田信長將傀儡將軍義昭逐出京都,結束了名存實亡的室町幕府統治。武田信玄死前遺言,下令家臣不得在他死後出兵攻戰,但是掌握著實際兵權的武田勝賴一意孤行,大舉進攻。天正三年(1575年)雙方在長筱會戰,武田軍大潰,幾近全軍復沒。天正十年(1582年),武田氏的勢力徹底被織田信長所摧毀。
《影武者》的故事就發生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上。片中的“影武者”,實際上就是一名替身,更確切的說法應該是“飾演者”。影武者不僅要在面貌、體態、著裝等外在形象上類似於他所飾演的人,而且要在言談、舉止和氣質上無限接近。他要代替他所飾演的人出現在任何可能的場合,包括商討機密的會場,箭矢橫飛的前線,戒備森嚴的庭院,甚至是一個對他來說完全陌生的女人的臥榻之側。“影武者”的一言一行都受到極端嚴格的限制與監視,以保證出演的逼真,符合被飾演者的意志,達到某個特殊的目的。
宏大敘事與歷史書寫
越是宏大的敘事,越是值得懷疑的,中國電影史中已經給我們提供了足夠多的案例來證明這個道理。這不是宏大本身的過錯,問題在於敘事的失誤。如何在尊重語法的前提下避免空洞與虛偽,是至關重要的。毫無疑問,就這一方面來說,《影武者》是一個堪稱經典的成功範本。
影片中對於室町時代晚期日本社會圖卷的鋪陳波瀾壯闊,清晰地再現了戰國大名爭奪天下的過程——這是日本史上從“應仁之亂”(應仁元年,1467年)到豐臣秀吉統一日本期間(天正十八年,1590年)最為動盪的時期。對於以戰爭為題材的影片而言,敘事的陷阱較之其他題材的影片更多。要么成為視覺期待的盛大筵席,要么成為意識形態的高音喇叭,前者的教訓如《珍珠港》,後者則可以用愛森斯坦的很多作品來做說明——雖然他的《戰艦伯將金》長久而廣泛地被當作剪輯技巧的經典而學習。另一種企圖以戰爭來探討人性的美好願望則往往因為對戰爭本體的忽略而落入尷尬的境地,中國內地導演馮小寧的作品即屬此類。對於龐大而遙遠的古代戰爭的回憶,則更是這樣。不僅如此,涉及到古代戰爭歷史題材的影片往往還被認為是負有傳達本民族精神與文化的任務,電影的創作者在這樣的閱讀期待之中,於影片所要塑造的人物群像之間左顧右盼,將龐雜的歷史演變為凌亂的線索,最終只剩下一堆虛張聲勢的膠片等待剪輯。《影武者》成動地避開了這樣的困境。
影武者是一個飾演者,但是這個演員卻是歷史所選擇的。當個人命運遭遇歷史文化語境之時,就產生了一系列的衝突。是個人面對歷史投降,完全放棄個體的思索,還是歷史因為個人而改寫,在偶然性的鏈條中因為個人品質中的某些必然因素而改變方向?這樣的衝突給《影武者》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來將關於歷史文化的宏大敘事與個人關照結合起來。
武田信玄的“影武者”,他的弟弟信廉,偶然在鐮成河畔的刑場上發現了一個即將被處死的犯人,長相與信玄非常相似的一個竊賊。信廉覺得這個人可以擔任信玄的“影武者”,就他解救回來。此時的武田信玄正雄心勃勃地準備與織田信長和德川家康的聯軍一決雌雄,奪取天下。征戰途中,信玄在野田身遭而死。武田信玄死前叮囑家臣,在他死後三年中不得走露風聲。為了遵守信玄的遺言,信廉帶回來的影武者從此粉墨登場。作為武田氏主公的替身,他在眾家臣的操縱中將自己移植到武田信玄的位置上。他假扮信玄檢閱三軍,主持會議,坐鎮疆場,甚至還要躺在信玄的寢室中睡覺。武田信玄已死,但他的旗幟和影子必須活著,否則日本的歷史就必須重新書寫。
影武者跟隨著武田信玄的舊部山縣昌景等人南征北戰,攻城略地,見證了武田氏的強大、衰微和最終復滅的全部過程。親歷歷史,在影片中成為有權言說歷史的資格憑證——和我們慣常所見到的同類影片不同,歷史在這裡不僅是言說的背景,而且還是言說的目的。
讓我們簡單地考察一下《影武者》攝製的時代背景,或許有助於了解這一點。影片應該算作是黑澤明的後期作品,拍攝於1980年,資金來源於法國和美國。之所以特別提出影片的拍攝資金,是因為這時候雖然日本崛起為世界經濟強國,但是電影工業卻開始嚴重萎縮,即在黑澤明前期與之多次合作的東寶公司,也開始大量縮減電影生產資金。“此時最有利可圖的是類型電影,主要有功夫片、強盜片、科幻片、災難片和軟性色情片”(克莉斯汀.湯普森、大衛.波德維爾著,陳旭光、何一薇譯,《世界電影史》,第62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當時轟動一時的影片是諸如市川昆的黑幫電影《犬神家族》、大島渚的軟性情色電影《感官王國》以及石京聰戶、冢本晉也等呈現荒誕暴力的影片。黑澤明在此時拍攝一部敘述日本歷史的電影,顯然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舉動。
到了拍攝《影武者》的時候,黑澤明放棄了他以前的精緻構圖,開始大量採用搖拍技法,將宏大的日本歷史和同樣宏大的戰爭場面納入視野,再現了四百前的浩瀚圖卷。黑澤明是久負盛名的日本導演,他被潛在地要求表達日本文化,而不僅僅是贏得票房。在稍後的《亂》中,普通觀眾很難從中見到莎士比亞《李爾王》的影子,完全就是一部日本歷史演義。一個更有趣的事實是《影武者》獲得了坎城金棕櫚獎並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而《亂》只獲得了一項奧斯卡“最佳服裝獎”。當然,影片因為優秀才獲獎,並不是因為貨獎才優秀,但是這其中是否透露出了一些別的信息?
早在1967年,黑澤明曾與美國FOX公司聯合拍攝表現珍珠港事件的影片《虎.虎.虎》,但是黑澤明的創作思路與製片方的商業實用主義大相逕庭,最終被製片方從導演的位置上更換下來。日本影評家佐藤忠男在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說:“儘管傾注很大熱情的工作半途中斷而不能不為之深感遺憾,但我不由地想,黑澤明導演美國電影的失敗,對他來說不僅不是一件難為情的事,說句可能不夠禮貌的話,恰恰是一件好事。我希望黑澤明創作日本自己的電影,成為偉大的日本電影導演。”(佐藤忠男著,李克世、崇蓮譯,李正倫校,《黑澤明的世界》,222—223頁,中國電影出版社,1983年版)
《影武者》顯然就是“日本自己的電影”,這絕不僅僅是因為它複寫或者想像了日本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對日本民族品格的開掘,是對不同的文化群落在日本史上所表現的不同症候的透視——這是由“影武者”完成的任務,也是本文所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
個人關照與文化認同
在影片開頭的一個令人驚異的長鏡頭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黑澤明前期創作的痕跡:適當的機位和精緻的構圖——鏡頭中的三個人物呈不等邊三角形——在平面上開創立體感最有效的途徑。三個人幾乎就是一個人,同樣的禿頂,同樣的鬍子,同樣的衣服,除了不同的身份以外,再沒有什麼不同。但是身份代表了一切。端坐於三角頂端的是武田氏的首領武田信玄,處於中間左邊一角的是信玄的弟弟,曾經做過他的影武者的信廉,處於最下方右邊一角的是偶然找到的可以充當另一個影武者的竊賊——除了竊賊和影武者這兩個稱呼之外,他連名字都沒有。
這名竊賊一開始並不想做影武者,在威脅之下,才被迫充任了這個角色。他依然“賊”性不改,想盜取財寶逃走,卻意外地發現了武田信玄的屍體。武田氏的家臣決定要放走他,但他在看到武田信玄的屍體被拋入湖中的時候卻又萬般哀求,由他來繼續充當信玄的影武者。
充當影武者,必須完全放棄自我,按照他人的標準來重新塑造自己,箇中滋味他早已嘗過,為什麼在重新回歸自我的路上他又突然轉向呢?實際上這個放逐自我的過程恰恰是重塑自我的過程,就象日本佛教里也承認的涅盤一樣,正是在喪失之中才有獲得。在充任影武者之前,這名竊賊擁有自己的判斷標準和行為原則。在他看來,真正罪惡的是攻城略地的武田信玄,這樣的人才是兇手,他自己只不過一名小小的竊賊而已。他對自己的行為毫不隱諱,也根本沒有打算改變自己的竊賊身份,所以才會在充當影武者的初期,還準備盜寶而逃。他承認自己是賊,並且對這種身份不感到絲毫的恥辱。後來他目睹了武田氏的家臣們遵照信玄的遺囑,將這個曾經號令一方的霸主的屍體沉入湖中,他突然改變了主意,苦苦哀求武田信廉再給他一次機會,讓他來充當影武者。在他跪倒在信廉腳下的那一刻起,他已經徹底放棄了賊人之心,另一個武者之心在他身上復活了。
克莉斯汀.湯普森與大衛.波德維爾合著的《世界電影史》中認為《影武者》“描述了由於無謂的權利之爭社會秩序遭到了摧毀”。這種概括只不過是該書作者站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上遠眺日本歷史而得出的簡單判斷而已。在武田氏的部隊被織田氏的火槍摧毀之時,日本列島被歐洲人發現才僅僅三十年(安東尼奧.伽爾凡著《世界探險史》記載,1542年,亦即日本歷天文十一年,葡萄牙人發現了日本列島)。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日本民族根本不可能受到多少西方文化的浸染。黑澤明的《影武者》也並不是一個符合西方文化經驗的東方歷史想像文本。對於日本歷史文化稍加關注,就會發現上引觀點的荒謬所在。
影片中所描述的事件發生在天正年間,也就是日本思想史上的第五個歷史時期——“經過織田——豐臣時代到德川時代”(永田廣志著,陳應年等譯,《日本哲學思想史》,第14頁,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的前期。就在織田氏徹底消滅武田氏勢力的前一年,耶酥會派往日本傳教的巡察師範禮安(AlessandroValignano)才得以見到織田信長,被允許傳教(鄭彭年著,《日本西方文化攝取史》,第10頁,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而佛教卻早已有影響了日本好幾百年,到鎌倉時代,日本禪宗的影響更大。日本禪宗強調:“‘即心是佛’,把可以叫做知的直觀那種恣意而空洞的真理感看作至高無上,和以滅絕人性使人心如木石為特點的克己主義確實適合武士階級的心理。在鎌倉時代以來開始形成的武士道中可以發現不少禪宗的影響,這決不是偶然的”(《日本哲學思想史》,第18頁)。
在影片中,我們看到作為影武者的賊人就是在看到武田被投入湖中的剎那間脫胎換骨的。就在此前一天,他還打破大瓮準備偷竊一些財寶逃走,但在他看到運載信玄屍體的小船在大霧中空空如也地返回時,卻一下子跪倒在地,請求再次充當影武者。這種另人費解的舉動或者正可以用禪宗的“頓悟”來解釋。是武者之心在頃刻間摧毀了他的賊人之心。《正法藏眼》中說:“一切諸法森羅萬象,率皆唯此一心,無所不包,無所不容。”影武者在跪倒的那一刻起,即開始了從喪失到重獲的過程。也正因為如此,他在後來扮演武田信玄的日子裡才能越扮越象,以至於不僅信玄的寵妾不能辨識,就曾經的影武者,了解全部內情的武田信廉也感到驚訝。
這名影武者到此時已經完全被武士道的文化品格所改變,“義”、“勇”、“仁”、“誠”等武士的德行不再是他所詛咒的“兇手”的德行,而內化為他內心的道德基礎和行為準則。影武者理解了武田氏“風”、“火”、“林”三軍的內涵,並且為武田信玄“不動如山”的旗幟所深深震撼,他甚至欲圖駕馭那匹只有信玄才能控制的黑馬,可惜從馬上摔下來,被受驚了的妻妾們認出了他的真實身份。影武者受盡了侮辱之後,被驅逐出門。武田氏的軍隊最終戰敗,全軍復沒,屍橫遍野,早已被驅趕走了的影武者卻在這時候出現在戰場上,朝著敵人的槍口衝上去。沒有人還能在這裡認出這個赴死的人是個竊賊,當他中彈倒下的時候,我們只能說一個武士殉道了。
黑澤明的《影武者》就是一部關於個人關照和文化認同之間的悲劇,影片所蘊涵的巨大張力是來自於文化品格對於個人意志的重新塑造,以及這種重新形成的文化人格的被迫喪失,而絕不是用西方文化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對日本歷史實施的強行改寫。作為西方文化代表的基督教“不久竟被織田信長利用作為對抗佛教的力量。但是豐臣秀吉時代以來基督教遭到禁止,特別在德川時代初期遭到了嚴禁”。不僅影片的歷史背景中,西方文化的影響微乎其微,就是在影片所敘述的故事中,上引西方學者的判斷也不能得到多少印證。與此相反,在影片結尾處那一組表現織田信長(與西方/基督教文化關係密切)的對手武田信玄(與佛教/東方文化關係密切)戰敗的鏡頭中,我們卻感受到了悲壯所帶來的感染力。
內容介紹
影片講述的是日本戰國時代發生的驚心動魄的戰鬥故事。通過展示當時政治、軍事鬥爭的錯綜複雜,以及糾纏不清的人事矛盾,加上激烈的戰爭場面,烘托出了“影子武士”的偉岸形象,仿佛一部悲壯的史詩。影片耗資巨大,各項資金共去二十五億日元之巨。影片為該年度日本十大賣座影片第一位,曾獲1980年《電影旬報》十佳獎第二名,第33屆坎城國際電影節(1980年)金棕櫚獎,併入選日本名片200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