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奧拉夫·H·豪格
奧拉夫·H·豪格豪格的詩具有典型的北歐特徵,樸質、抒情的語言中透露出深刻的哲理,體現出以事物的片斷來概括事物的整體的特點,對詩人自己來說,“幾滴水”、“一粒鹽”才是人類與世界最美好的聯繫,成為對這個物慾橫流的現實社會的抵抗和精神安慰。他的詩已經被譯成了數十種文字,在歐美具有較大的影響。
生活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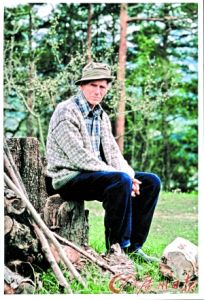 挪威陶淵明很“瘋”很中國
挪威陶淵明很“瘋”很中國避世而居、窮困潦倒、詩人身份——某種程度上,豪格跟中國古代田園詩人陶淵明非常相似。更何況,豪格與中國古代幾位詩歌巨人如屈原、李白、王維、陶淵明等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他的詩作《陶潛》中,他甚至“放肆”地表露著自己對陶淵明的喜愛:“假如有一天,/陶潛來看我,我要/給他看我的櫻桃樹與蘋果樹。/他最好春天來,/在果樹開花的時候。然後/我們在陰涼處坐下,喝一杯蘋果酒……”
正如豪格自己所言,平常的日子,“幹完活可以煎醃肉,讀中國古詩。”豪格一生鍾情於中國道家哲學和古典詩歌。
早在1931年,21歲的豪格就在一本《除草手冊》的書頁上抄錄了三段《道德經》。
飽受精神病困擾
豪格生前的健康狀況並不好,一再發作的精神病始終困擾著他,甚至幾度入住精神病院。當豪格住進精神病院,他無法寫作,不過,在他意識恢復之後,他會寫出自己瘋癲狀態下的詩篇,其中深層的含義曖昧不明,他自己也從未向任何人透露過。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門前》:“你問我認不認識中國?/你想問就問吧。/我在中國的/門外等了許久。/那扇門黃顏色,/麵包片就來自那裡。”
作品特點
豪格是極少數如艾米莉·迪金森那樣深居簡出的詩人,一生從未離開過家鄉,更不曾遠行。然而藉助紙上的旅行,他坐在北緯61度的家中,卻到達了許多地方,與不同國度的人們相遇。但最讓他醉心神往的,恐怕就是中國。1931年,21歲的年輕園丁豪格在一本名為《除草手冊》的小冊子裡抄錄下三段《道德經》中的語錄。從那時起,他便為中國哲學所吸引,但真正接觸到中國古典詩歌,則要到50年代初期。他1961年出版的詩集《在老鷹的草叢上》中,收入了兩首寫中國古代詩人的詩,一首是《屈原的故事》,另一首是《致李白》。1962年,豪格得到一本企鵝版《中國詩選》,那是第一本在西方廣泛發行的英文中國詩集。他在日記中說,那年整整一個夏天他都沉浸在這部詩選中。
如今,他的詩終於來到中國。豪格的第一本中文詩選《我站著,我受得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挪威漢學家哈羅德·勃克曼、詩人西川和勃克曼的妻子劉白沙共同翻譯。在2009年2月28日的新書發布會上,挪威駐華大使司文先生說,奧拉夫·豪格從沒有機會拜訪中國,但他的詩歌受到中國詩歌很大影響,他的詩作能與中國讀者見面是一大快事。
翻譯豪格的詩並不容易,因此當勃克曼決定要把豪格的詩帶到中國時,劉白沙覺得他是瘋了:“豪格的語言比較難懂,他用的是基於古老方言的西挪威語,而且勃克曼要將其翻譯成並不是自己母語的中文,難度更大。”在奧斯陸大學訪問的清華大學教授汪暉向勃克曼介紹了中國詩人西川。勃克曼聯繫到西川後,又專程與他見面。在勃克曼西方式的堅持下,豪格的“中國之旅”真正啟動:勃克曼與劉白沙將詩粗譯成中文,然後交予西川加工。四處旅行的西川將譯稿隨身帶著,機場、飛機上,旅館裡,他一次次打開手提電腦,一次次斟酌詞句,與豪格交心。逐漸地,西川認識了豪格,他在譯後記里寫道:“豪格的詩歌帶給我感動、驚訝和驚喜,甚至與我內心中的某些東西深為投契。”
自然之美經常出現在豪格的詩里,然而現實中,他也為季節流轉、天氣變化擔憂。豪格子承父業,守著父母留下的一個小農場,以種果樹和為鄰人們做園藝活為生。他終日在土地上勞作,日子過得簡單樸素,有時甚至頗為艱辛。在北緯61度種植蘋果樹堪稱美事一樁,但收入可憐。說起來,豪格做果農也算學有所用。19歲時,他進入當地的園藝學校,學習了3年後,又在國家農業學院和一家實驗農場當了4年的學徒。從童年起,豪格就飽讀文學書籍。
豪格在學校里學過英語和德語,又自學了法語,他將許多西方詩人的作品翻譯成挪威語,比如葉芝、保羅·策蘭、荷爾德林等等。事實上,豪格的詩吸取了各種文化的營養,不但受到西方古典和現代文學的滋養,而且涉獵了不少中國和日本的詩歌。
豪格在詩中說:“好詩/應該有茶葉的味道,/或者生土與新柴的味道。”(《我有三首詩》)“幹完活可以煎醃肉,/讀中國古詩。”(《平常的日子》)詩里對中國的提及並不偶然,他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簡潔之美興趣頗深。受到中國古詩的影響,豪格後期作品呈現出簡短而直接的風格,許多詩短小如日本俳句,寥寥數筆,但蘊含著許多思想和哲理,如《大鐵錘》、《鋸子》等。在詩人西川看來,這樣的詩在西方詩歌語境裡夠極端:語言平易,詩思機智,詩意盎然。
豪格在幻想中與陶淵明神交:“假如有一天/陶潛來看我,我要/給他看看我的櫻桃樹和蘋果樹。/他最好春天來,/在果樹開花的時候。然後/我們在陰涼處坐下,喝一杯蘋果酒。/我可能給他看一首我的詩/—假如我找得到他喜歡的詩。/今日飛龍在天,留下毒物與濃煙/在他那個時代,龍飛的聲音更輕些,/有更多的鳥兒啾啾叫。/我這裡沒什麼他不能理解的事物。/他可能想隱居在這樣的小果園,/但不知他是否會避世而問心無愧。”(《陶潛》)西川說:“在讀了他一定數量的詩歌以後,我把他看成我們中間的一員,而他自己似乎也這樣看。”
生活中許多稀鬆平常的小事,在豪格眼裡都顯得格外珍貴,自然,他用詩的語言小心翼翼地把這些瑣碎的經驗保留下來。豪格關心著寒秋里未摘的蘋果,眷戀於冬天早晨暖烘烘的屋子,沉醉於大海的深邃與寂寥,也感嘆季節的降臨和消逝。每一件事物,無論微小還是宏大,都在他的筆下發出熠熠光輝。豪格的許多關於日常生活經驗和自然萬物的詩都通過對極細微處的觀照,創造出一片平靜安詳的天地。那種感覺,就像《樹葉小屋與雪窟》那首詩中寫到的,這些詩句“僅僅是/幾個詞兒,偶然地/疊在一起”,但讀詩的人卻好像“臨時有了間小屋”,溫暖而安全:“想到幼年的樹葉小屋:/我們爬進去,坐下來/聆聽雨聲,/知道荒野里只有我們自己,/我們感到鼻子與頭髮上的/水珠——/或者是聖誕節時的雪窟/我們爬進去,用一隻黃麻袋/封住通道,/點上蠟燭。在寒夜裡/我們留在那裡。”
豪格的詩還有很大一部分探討的是人生和真理,富有洞見,甚至顛覆而創新。人生路上,他是一位孤獨而固執的逆行者,“在人跡不到的路徑上你漫遊了多年,/終於抵達了高處”(《在高處》),“你看,我站著。/你看,我受得了。/你看,我還是會站在這裡。”(《你看,我站著》)這樣的不妥協隨處可見。而在對真理的探索中,他發現真理是“一隻易驚的鳥”,他說“請不要給我全部真理”,只要“一線微光,一滴露水,一點點”,便足夠。
豪格的人生經驗並不複雜,他和母親在一起住了很久,晚年結識了熱情的女藝術家布迪爾·卡普蘭。卡普蘭非常喜歡豪格的詩,主動追求豪格,與他通信很久。兩人逐漸發展出一種密切的關係,在1978年結婚。
1994年一個尋常的下午,86歲的奧拉夫·H·豪格靜靜地坐在家中一把椅子裡,沒有任何跡象地離開了這個世界。葬禮儀式過後,一輛馬車把他拉上山。每個人都注意到,一匹小馬駒在馬車旁歡快地跟著它的媽媽和棺材跑了一路。
卡普蘭在整理豪格的遺物時發現他從15歲起就開始寫日記,堅持了整整70年。這些日記分5卷出版,有4000多頁,成為挪威已出版的最大部頭的日記集。在豪格的家鄉,人們每年都為紀念他舉行盛大的節日聚會,許多挪威的青年詩人來到烏爾維克,使這個北歐小村莊變得異常熱鬧。
豪格曾經在詩里幻想,“我在中國的地位很高”,這句話今天讀起來,不再那么痴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