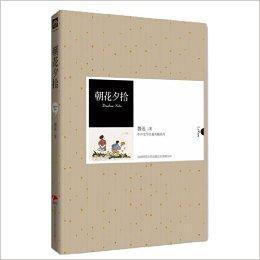內容簡介
《朝花夕拾》特別收錄了包括《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為了忘卻的記念》、《咬文嚼字》等在內的諸多魯迅的精品文章。每篇文章都生動地向讀者描繪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畫面,文筆深沉雋永,是中國現代散文中的經典之作。在刻畫那些舊社會的不幸者時,魯迅不僅僅是著眼於他們在物質上的貧窮和落後,更多的是著眼於他們在精神上的麻木和愚昧。所以,這些文章實質上就是對現代中國人靈魂的偉大拷問。
《朝花夕拾》:魯迅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開創者,他的文章筆鋒犀利、針砭時弊,讀後能發人深思。《朝花夕拾》是魯迅所寫的唯一一部回憶散文集,原名《舊事重提》。這本散文集在業內獲有相當高的評價,是青年朋友們最熱衷的書籍之一。我社為讓讀者能夠讀到更多更好的作品,便將魯迅文章中的精華部分集結成冊,希望能給讀者帶來愉悅的讀書享受,也同時將它推薦給廣大中學生朋友。希望度過魯迅的文章,能夠讓他們更清楚的了解社會、文化和生活
作者簡介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為豫才,我國現代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世界十大文豪之一,被譽為現代文學的一面旗幟。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說、雜文為主,代表作有:小說集《吶喊》、《彷徨》等,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詩集《野草》,雜文集《熱風》、《華蓋集》、《華蓋續集》、《南腔北調集》、《三閒集》、《二心集》、《而已集》、《墳》等。其作品共有數十篇被選入中、國小語文課本,並有多部小說被先後改編成電影。魯迅以筆代戈、奮筆疾書、戰鬥一生,被譽為“民族魂”。“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是魯迅先生一生的寫照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導讀
魯迅(1881—1936),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樟壽,字豫才,後改名樹人,浙江紹興人。出生於破落士大夫家庭。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開始使用的筆名。魯迅在1898年到南京求學,1902年留學日本學醫,後痛感於醫治麻木的國民精神更重於醫治肉體病痛,便改行提倡文藝運動。1909年回國,在杭州、紹興任中學教員o1912年到北京,在教育部任職,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講師o 1918年參加《新青年》編輯工作,並在《新青
年》上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其後又發表了《孔乙己》、《藥隊《阿Q正傳》等著名小說,並撰寫大量雜文、散文,批判舊思想、舊道德,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1923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們內喊》,成為中國新文學的奠基作。1926年8月起先後任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教授。1927年10月定居上海,從事文學寫作,參與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為中國左翼文化運動的實際領導者和旗幟,在與國民黨文化“圍剿”的鬥爭中成為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生前出版小說集三種、散文集兩種、雜文集十五種、通信集一種、文學史著作兩種。魯迅在翻譯外國文學和整理中國古籍方面也成績卓著。其全部著譯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彙編為《魯迅全集》(十六卷)、《魯迅譯文集》(十卷)、《魯迅輯錄古籍叢編》(四卷)。
《朝花夕拾》是魯迅1926年所作的回憶散文集,共10篇。最初在《莽原》雜誌發表時總題目為“舊事重提”,1927年編集成書,改為現名。魯迅在寫作這些作品時正經受著北洋軍閥當局和各種敵對勢力的嚴重壓迫。1925年他因支持學生運動,受到“正人君子”們各種“流言”的攻擊和誹謗。1926年3月18日北洋軍閥政府槍殺進步學生,,魯迅受反動政府通緝,不得不到廈門大學任教,後又受守舊勢力的排擠。在這樣的處境中魯迅曾說:“這時我不願意想到目
前;於是回憶在心裡出土了。”這10篇作品,前.5篇寫於北京,後5篇寫於廈門。雖然是回憶文章,但都反映著當時社會鬥爭的痕跡。
《朝花夕拾》的作品記述了作者童年的生活和青年時求學的歷程,追憶那些難於忘懷的人和事,抒發了對往日親友和師長的懷念之情。作品在夾敘夾議中,對反動、守舊勢力進行了抨擊和嘲諷:第一篇作品《狗·貓·鼠》是針對“正人君子”的攻擊引發的,嘲諷了他們散布的“流言”,表述了對貓“盡情折磨”弱者、“到處噑叫”、時而“一副媚態”等特性的憎惡;追憶童年時救養的一隻可愛的隱鼠遭到摧殘的經歷和感受,表現了對弱小者的同情和對暴虐者的憎恨。
《阿長與》憶述兒時與保姆長媽媽相處的情景,描寫了長媽媽善良、樸實而又迷信、嘮叨、“滿肚子是麻煩的禮節”的性格;對她尋購贈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繪圖《山海經》之情,充滿了尊敬和感激。文章用深情的語言,表達了對這位勞動婦女的真誠的懷念。
…… --此文字指本書的不再付印或絕版版本。
名人推薦
由魯迅最早的藏書想起
魯迅最早的藏書,是一部木刻繪圖《山海經》:四本小小的書,紙張很黃,刻印都十分粗拙,圖像差到幾乎全用直線湊合,連動物的眼睛都是長方形。可是年幼的魯迅如獲至寶: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一腳的牛,沒有頭而“以乳為目、以臍為口”的怪物,遠古神話世界的奇烈想像透過粗鄙的紙頁噴薄而來,讓心智初開的少年驚慕不已。幾十年後,念及不知何時散佚的這最初的收藏,早已年過不惑的魯迅在一冊思憶兒時故鄉生活的集子裡寫道,這四本書,乃是我最初得到、最為心愛的寶書。
這四本小書僅僅是一個起點。魯迅的藏書單上隨後添了石印的《爾雅音圖》和《毛詩品物圖考》,《點石齋從畫》和《詩畫舫》,又有了冠冕堂皇的《文昌帝君陰騭文圖說》和《玉曆鈔傳》,畫的是冥冥之中賞善罰惡的故事。此外,《山海經》另買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圖贊,綠色的畫,紅色的字,比早先那部精緻許多。少年魯迅不僅多方搜羅,更炮製自家品牌的繪本:用一種“荊川紙”,蒙在小說的繡像上描摹,是他在三味書屋最愉快的消遣,尤其當先生讀書入神的時候。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卻不少,魯迅日後自謙地說,比如《蕩寇志》和《西遊記》的繡像,各有一大本,後來賣給一個闊綽的同窗。
用學界近年流行的一個觀點來看,魯迅自啟蒙時代便表現出一種對“視覺文化”的偏愛。這種偏愛亦伴隨他負笈東瀛,最突出的例證之一(“之一”二字或可刪去),便是如今廣為人知的魯迅先生棄醫從文的故事:一段日俄戰爭期間的時事幻燈片,給俄國人做偵探的中國人被日本人捕獲槍斃,一群中國人圍觀;影片之外,仙台醫學院課堂里唯一的中國人自覺來到人生的轉捩點。這箇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耳熟能詳的典故,在周蕾Primitive Passions一書中獲得了一種新的解讀:魯迅顯然對給他帶來巨大刺激的這種新興媒介的本質認識不足,周蕾指出,不然他怎么會在親身體驗了視覺影像的深刻震撼之後,反諷地做出投身文學的決定?作為電影領域的學者,周蕾的這一觀察是敏銳而獨到的。然而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在於,文化研究多著眼於照片、電影、海報、月份牌及宣傳廣告等,其由此構建的“視覺文化”的概念,是否同樣適用於或者說足夠駕馭另一類從製造年代到性質都極為不同的視像文本,如繪圖《西遊記》、《玉曆鈔傳》甚至《山海經》?
關於魯迅最早的藏書的故事收錄於《朝花夕拾》。無論魯迅如何被後世的文學史家塑造成一位鮮明而徹底的新文化的播種者與舊文化的掘墓人,一個讀過其主要文學作品(包括短篇小說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散文詩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及片段日記書信的細緻而誠實的讀者,多少都能從字裡行間捕捉到這位中國現代文學之父對巍巍五千載文明傳統的復調而曖昧的態度;尤其在他追憶兒時江浙歲月的散文集《朝花夕拾》里,更讓人一窺在新舊世界嬗替之際,最後一代為傳統文化餘暉所浸潤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成長軌跡。與那個曾被無節制地神化英雄化經典化的魯迅相比,我想,更讓我感興趣的是那個正值盛年卻自囚於幽僻的紹興會館一宿接一宿抄古碑抄佛經,那個重寫中國小說史並對上古的神話寓言和宋以前的志怪傳奇情有獨鍾,那個在支持新文學運動的同時始終沒有間斷文言詩的創作,以及那個在四十歲上憶及故鄉迎神賽會上的勾魂無常,親切地稱道其人情味夠得上做一個“真正的朋友”的魯迅。李歐梵在《鐵屋中的吶喊》一書中談到,概括地說,魯迅在傳統文化上的口味是在所謂的“大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之外的,他的偏好更趨向於中國文化里的“反傳統”(counter-tradition),即與自孔孟到朱熹王陽明的儒家正統構成對立或保持疏離的思維與情感方式。舉例來說,在小說文類里,魯迅尤為唐以前、即宋明理學發端以前的作品所吸引,在詩人中他最傾心的是以瑰奇的想像和澎湃的靈魂訴求著稱的屈原,以散文而言他推崇魏晉古風遠勝唐宋八大家,以閱史而言他對野史雜說的興味比對正史濃厚得多。
李歐梵以傳統─反傳統為軸丈量魯迅相對於中華文明傳統的定位,這種兩極對立的視角本身便帶有現代文學領域裡根深蒂固的割裂與對抗的思維模式的烙印。然而針對“大傳統”,還有另一種另類的可能,即“小傳統”(the little tradition)。自我身份意識清醒的、訴諸理智的“大傳統”以文字書寫為載體,通過在文史、思想與藝術上的不斷構建表達出社會與文明總體的外露的理想;而未必自覺的、不倚賴思辯和書寫的“小傳統”寄身於不識字的階層,並在代代相傳的民間信仰與行為慣式里滋衍不息──魯迅的第一套藏書在更大意義上正是後者的一個縮影。更典型的是,這套繪圖《山海經》不是從書店尋獲的,而是魯迅幼年的乳母,一個連自身名姓都未留下的下層女性在告假返鄉時,不知從什麼地方弄來的。“哥兒,有畫兒的'三哼經',我給你買來了!”她這么告訴魯迅。長媽媽顯然沒有受過教育;然而在《朝花夕拾》另一處,魯迅說,即便不識字如阿長,一看《二十四孝圖》的圖畫也能滔滔講出一段事跡。
YING
2011-01-05 08:53:15 --此文字指 平裝 版本。
目錄
朝花夕拾
小 引
狗·貓·鼠
阿長與《山海經》
《二十四孝圖》
五猖會
無 常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父親的病
瑣 記
藤野先生
范愛農
後 記
時風詰論
記念劉和珍君
為了忘卻的記念
“友邦驚詫”論
拿來主義
咬文嚼字
論雷峰塔的倒掉
再論雷峰塔的倒掉
最藝術的國家
論“人言可畏”
論睜了眼看
文思博識
門外文談
論新文字
燈下漫筆
運 命
文床秋夢
學界的三魂
論辯的魂靈
慧語睿辯
世故三昧
清明時節
說“面子”
科學史教篇
文化偏至論
憶韋素園君
喝 茶
推的余談
臉譜臆測
雜談小品文
漫談“漫畫”
文摘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我家的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園,相傳叫做百草園。現在是早已並屋子一起賣給朱文公的子孫了,連那最末次的相見也已經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時卻是我的樂園。
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里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里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就有無限趣味。油蛉在這裡低唱,蟋蟀們在這裡彈琴。翻開斷磚來,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樑,便會拍的一聲,從後竅噴出一陣煙霧。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著,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何首烏有擁腫的根。有人說,何首烏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於是常常拔它起來,牽連不斷地拔起來,也曾因此弄壞了泥牆,卻從來沒有見過有一塊根像人樣。如果不怕刺,還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攢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遠。
長的草里是不去的,因為相傳這園裡有一條很大的赤練蛇。
長媽媽曾經講給我一個故事聽:先前,有一個讀書人住在古廟裡用功,晚間,在院子裡納涼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在叫他。答應著,四面看時,卻見一個美女的臉露在牆頭上,向他一笑,隱去了。他很高興;但竟給那走來夜談的老和尚識破了機關。說他臉上有些妖氣,一定遇見“美女蛇”了;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喚人名,倘一答應,夜間便要來吃這人的肉的。他自然嚇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卻道無妨,給他一個小盒子,說只要放在枕邊,便可高枕而臥。他雖然照樣辦,卻總是睡不著,——當然睡不著的。到半夜,果然來了,沙沙沙!門外像是風雨聲。他正抖作一團時,卻聽得豁的一聲,一道金光從枕邊飛出,外面便什麼聲音也沒有了,那金光也就飛回來,斂在盒子裡。後來呢?後來,老和尚說,這是飛蜈蚣,它能吸蛇的腦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結末的教訓是:所以倘有陌生的聲音叫你的名字,你萬不可答應它。
這故事很使我覺得做人之險,夏夜乘涼,往往有些擔心,不敢去看牆上,而且極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樣的飛蜈蚣。走到百草園的草叢旁邊時,也常常這樣想。但直到現在,總還沒有得到,但也沒有遇見過赤練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聲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園比較的無味;雪一下,可就兩樣了。拍雪人(將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羅漢需要人們鑑賞,這是荒園,人跡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來捕鳥。薄薄的雪,是不行的;總須積雪蓋了地面一兩天,鳥雀們久已無處覓食的時候才好。掃開一塊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篩來,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條長繩,人遠遠地牽著,看鳥雀下來啄食,走到竹篩底下的時候,將繩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頰的“張飛鳥”,性子很躁,養不過夜的。
這是閏土的父親所傳授的方法,我卻不大能用。明明見它們進去了,拉了繩,跑去一看,卻什麼都沒有,費了半天力,捉住的不過三四隻。閏土的父親是小半天便能捕獲幾十隻,裝在叉袋裡叫著撞著的。我曾經問他得失的緣由,他只靜靜地笑道:你太性急,來不及等它走到中間去。
我不知道為什麼家裡的人要將我送進書塾里去了,而且還是全城中稱為最嚴厲的書塾。也許是因為拔何首烏毀了泥牆罷,也許是因為將磚頭拋到間壁的梁家去了罷,也許是因為站在石井欄上跳了下來罷……都無從知道。總而言之:我將不能常到百草園了。Ade,我的蟋蟀們!Ade,我的覆盆子們和木蓮們!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著一塊匾道:三味書屋;匾下面是一幅畫,畫著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著那匾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著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不知從那裡聽來的,東方朔也很淵博,他認識一種蟲,名曰“怪哉”,冤氣所化,用酒一澆,就消釋了。我很想詳細地知道這故事,但阿長是不知道的,因為她畢竟不淵博。現在得到機會了,可以問先生。
“先生,‘怪哉’這蟲,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書,將要退下來的時候,趕忙問。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興,臉上還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學生是不應該問這些事的,只要讀書,因為他是淵博的宿儒,決不至於不知道,所謂不知道者,乃是不願意說。年紀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見過好幾回了。
我就唯讀書,正午習字,晚上對課。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卻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裡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臘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餵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裡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裡便大叫起來:
“人都到那裡去了?”
人們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
“讀書!”
於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念“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的,有念“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錯厥貢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書。後來,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靜下去了,只有他還大聲朗讀著:
“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座皆驚呢;金叵羅,顛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因為讀到這裡,他總是微笑起來,而且將頭仰起,搖著,向後面拗過去,拗過去。
先生讀書入神的時候,於我們是很相宜的。有幾個便用紙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戲。我是畫畫兒,用一種叫做“荊川紙”的,蒙在小說的繡像上一個個描下來,像習字時候的影寫一樣。讀的書多起來,畫的畫也多起來;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卻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遊記》的繡像,都有一大本。後來,因為要錢用,賣給一個有錢的同窗了。他的父親是開錫箔店的;聽說現在自己已經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紳士的地位了。這東西早已沒有了罷。
後記
我在第三篇講《二十四孝》的開頭,說北京恐嚇小孩的“馬虎子”應作 “麻鬍子”,是指麻叔謀,而且以他為胡人。現在知道是錯了,“胡”應作 “祜”,是叔謀之名,見唐人李濟翁做的《資暇集》卷下,題雲《非麻胡》。原文如次: “俗怖嬰兒曰:麻胡來!不知其源者,以為多髯之神 而驗刺者,非也。隋將軍麻祜,性酷虐,煬帝令開汴河,威 棱既盛,至稚童望風而畏,互相恐嚇日:麻祜來!稚童語 不正,轉祜為胡。只如憲宗朝涇將■,蕃中皆畏憚, 其國嬰兒啼者,以■怖之則止。又,武宗朝,閭閻孩孺相 脅云:薛尹來!鹹類此也。況《魏志》載張文遠遼來 之明證乎?”(原註:麻祜廟在睢陽。■方節度李丕即其 後。丕為重建碑。) 原來我的識見,就正和唐朝的“不知其源者”相同,貽譏於千載之前,真是咎有應得,只好苦笑。但又不知麻祜廟碑或碑文,現今尚在睢陽或存於方誌中否?倘在,我們當可以看見和小說《開河記》所載相反的他的功業。
因為想尋幾張插畫,常維鈞兄給我在北京蒐集了許多材料,有幾種是為我所未曾見過的。如光緒己卯(1879)肅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卅孝圖》——原書有注云:“■讀如習。”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稱四十,而必須如此麻煩— —即其一。我所反對的“郭巨埋兒”,他於我還未出世的前幾年,已經刪去了。序有云: “……坊問所刻《二十四孝》,善矣。然其中郭巨埋兒 一事,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訓。……炳竊不自量,妄 為編輯。凡矯枉過正而刻意求名者,概從割愛;惟擇其事 之不詭於正,而人人可為者,類為六門。……” 這位肅州胡老先生的勇決,委實令我佩服了。但這種意見,恐怕是懷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來已久的,不過大抵不敢毅然刪改,筆之於書。如同治十一年(1872)刻的《百孝圖》,前有紀常鄭績序,就說: “……況邇來世風日下,沿習澆漓,不知孝出天性自 然,反以孝作另成一事。且擇古人投爐埋兒為忍心害 理,指割股抽腸為損親遺體。殊未審孝只在乎心,不在乎 跡。盡孝無定形,行孝無定事。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今 之孝者難泥古之事。因此時此地不同,而其人其事各異, 求其所以盡孝之心則一也。子夏日:事父母能竭其力。
故孔門問孝,所答何嘗有同然乎?……”則同治年間就有人以埋兒等事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至於這一位“紀常鄭績”先生的意思,我卻還是不大懂,或者像是說:這些事現在可以不必學,但也不必說他錯。 --此文字指本書的不再付印或絕版版本。
序言
說明
《朝花夕拾》共10篇。前5篇寫於北京,後5篇寫於廈門。這些"回憶的記事"(《三閒集〈自選集〉自序》),記錄了作者從幼年到青年時期的生活道路和經歷,生動地描繪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畫面,成為研究魯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當時社會狀況的重要文獻。這些篇章,往事與現實糾結,敘述與議論交織,情感深摯,筆調雋永,是中國現代散文中的經典作品。
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增田涉見到魯迅,問研究中國文學應該讀什麼書,魯迅即以《朝花夕拾》相贈。魯迅1934年4月11日寫信給想翻譯此書的增田涉說:"《朝花夕拾》如有出版處所,譯出來也好,但其中有關中國風俗和瑣事太多,不多加注釋恐不易看懂,注釋一多,讀起來又乏味了。"
各篇最初以"舊事重提"為總題,陸續發表於《莽原》半月刊。1927年7月,魯迅在廣州重新加以編訂,並添寫《小引》和《後記》,改名《朝花夕拾》,於1928年9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為作者所編的《未名新集》之一,封面為陶元慶所繪。1929年2月再版。1932年9月第3版有未名社和上海北新書局兩個版本。
此次校訂以魯迅生前校定的版本為底本,並參校其他版本,注釋力求簡要。魯迅時代某些詞句和標點符號與現行用法不一致者,仍其舊,不做改動。 --此文字指 平裝 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