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簡介
《世界要案審判》收集了長達2500年30多個國家的司法案例,原來在各個不同的國家中,公正所詮釋的意義也不盡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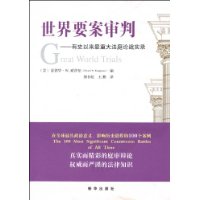
作 者:愛德華·耐普曼
出版社: 新華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9年05月
ISBN: 9787501187843
開本: 16開
定價: 58.00 元寫作意義
像任何一部百科全書一樣,本書的收集和編撰也經歷了一個複雜而艱難的過程,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一些主觀性,不足之處在所難免。自從1607年詹姆斯鎮建立以來,實際上在美國法庭上已經審理了不計其數的民事和刑事案件。有很多案件具有歷史或法律意義,或者因為某種原因引起了公眾廣泛的關注。為此,我試圖選擇最符合下面若干原則的200個案例。
歷史意義:該案件是否影響了美國的歷史進程?比如,斯科特訴桑福德案是邁向美國內戰的關鍵一步;波士頓謀殺案為美國獨立戰爭奠定了基礎。這兩個案件符合本條準則。
法律意義:該案件是否開闢了一個司法先例,或者對最高法院的裁決有里程碑似的意義?這樣的案例包括:山姆·謝波德案,它開啟了關於審判前公開性的先例,這一意義是十分重大的;嬰兒M案影響了代孕母親身份契約的有效性;吉迪恩訴韋恩懷特案使得最高法院做出如下規定:在刑事案件中,各州應為貧窮的被告無償提供辯護律師。
政治爭端:該案件是否使一個國家內部產生政治爭端?符合這條原則的案件包括:薩克-范澤蒂謀殺案,對激進分子和移民的敵意使該案審理受到了不良影響;尤利斯和艾絲爾·羅森伯格叛國案,芝加哥希文煽動反越南戰爭遊行示威案,都屬於此類案件。
公眾的關註:我們歷史上的很多案件因為當事人的名氣或者被指控罪行的性質都引起了全國的轟動。布魯諾·豪普特曼綁架林登堡嬰兒案,以及丹尼爾·希克爾斯、利茲·伯頓、哈里·肖、讓·哈里斯、帕蒂·赫斯特和查爾斯·曼森案均屬此類。
多謀善斷:有些案件之所以在本書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因為由一個或更多律師進行辯護的案件展示了高超的智慧和辯術,使這些案件具有了傳奇色彩。符合這一原則的案件包括:馬丁內斯訴戴爾·韋勒案,在此案中約瑟夫·考艾特運用了著名的反詰調查手段;利奧波德和勒布謀殺案中,克拉倫斯·達羅為其成功地進行了辯護;三件套裙公司縱火案中,麥克斯·斯杜爾被無罪釋放,這樣的結果始料未及。
蜚聲文壇:有些案件刺激了小說家、劇作家、影視編劇、非小說類作家,甚至是詞曲作家的靈感,他們的作品比案件本身對公眾產生了更大的影響,使這些案件永遠保存在了文學殿堂中,它們包括:切斯特·吉勒特謀殺案,薩勒姆·韋奇克萊夫特案,喬·希爾謀殺案,司考普斯“猴子”案,以及理察·希科克/佩里·史密斯謀殺案。
《世界要案審判》收錄的案例時間跨度長達2500年,其中體現了30多個國家的法理學和司法制度。同時在收錄案例中,《世界要案審判》對於“審判”一詞作了最廣義的理解,就是審判這個詞本身,還不用說公正的審判——在不同的社會裡也存在著巨大差異。審判一直是大眾興奮的焦點和公眾參與的儀式,同時也是活生生的人生戲劇。
介紹
從殖民時期直至今天,法庭判決一直是解決美國社會爭端的最終手段。美國歷史上很多重要的轉折點都是在法庭上發生的——從約翰·彼得·曾格的所謂誹謗紐約殖民地英國長官案到禁止各州允許在孕前期實行墮胎的羅訴韋德案。
審判也一直是大眾興奮的焦點和公眾參與的儀式。同時,也是活生生的人生戲劇。美國人蜂擁到法庭里,為正義歡呼鼓舞,為邪惡義憤填膺,或受到激勵,或受到教育,或為洗滌靈魂,或只是為一時之娛。人們也時刻關注著各種媒體的報導和介紹。在通訊系統還不那么發達的時代,對大多數鄉村民眾而言,法庭是少數可以獲得審判信息的渠道之一。實際上,法官、牧師和新聞記者一直在堅持不懈地譴責那種地方以至全國聞名的案件審判過程中出現的“鬧劇”氣氛,使這個詞頻頻出現在各種新聞報導中。在距離今天更近的時代,真實的和虛擬的審判成為影視製片商和節目製作人的主打產品。今天,有線電視“電視法庭”網使得那些審判癮君子們從來沒有轉換頻道的打算。
雖然審判像戲一樣牽動人的神經,但在我們社會中它畢竟有著更為嚴肅的目的:當個人或其他法律實體,比如公司,踐踏了另外一個人或集體的受法律保護的權利的時候,法律審判提供了一個維護公共秩序的機制。在這種意義上講,審判滿足了人們懲罰罪惡的需要,即使是敗訴的一方也能感覺到自己畢竟有一個“對簿公堂”進行申訴的機會。
因此,審判是美國司法體系的核心內容。當然,通過對事實的審判——訴訟——來解決爭端的過程只是司法實踐中的一個領域。被訴訟當事人提起訴訟的案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最後進行了審判。實際上,大多數並非訴訟當事人的律師都在致力於勸說當事人避免進行審判,建議他們如何按照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則起草一個法律檔案,比如說契約。
要理解《美國要案審判》中所敘述的案件的“要”的含義,需要對法律的分支、美國司法制度的歷史和輪廓、以及審判方式所依賴的程式和證據規則有基本的了解。儘管我們的編輯和撰稿人已經儘可能把法律術語變成了大眾語言,但有些法律術語依然沒有合適的字樣或詞語加以解釋。讀者在本書的末尾可以看到這些詞語的注釋詞表。
或許法庭最重要的性質是它是一個公共實體。在每一個案件中,法庭必須對事實做出判斷。在判斷它們的法律意義的時候,法庭不僅是在為訴訟當事人服務,而且是為更廣大的社會群體服務。在按照法律解決某一個具體爭端的時候,法庭為那些在未來可能遇到類似問題的人們提供指導,從而預先阻止一些可能潛在的訴訟。
所謂法官依判例判定的新方法——與立法相對——是我們這種司法體系中習慣法的自然的副產品。按照這種方法,現在的案例按照以前的判例的結論進行判定。這種“習慣法”是在數代法官的無數個判定的基礎上形成的複雜的規則體系,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英國的中世紀。因此,習慣法早於立法機關的確立。立法機關的首要任務是起草那些由以往案件所得出的經現代法庭解釋和套用的法律規則。
相比而言,“民法”是由羅馬的成文法典發展而來的,今天已成為西歐(當然除了聯合王國)以及路易斯安那普遍適用的法律制度。儘管今天調節公法或刑法(其中政府有著最直接的利益)、私法或民法(直接關係到個體的利益)的法規數量在不斷增加,習慣法制度在我國的其他地區占據主導地位。
英國的法院制度原封不動地移植到了殖民地美國。在17世紀的美國,立法和審判被認為是一回事。在英國,議會被認為是最高法院。然而,殖民地開始形成自己的分層法院制度。金字塔的尖端是殖民地立法機關,主要功能是抗訴法院。在它下面的是一個高級法院網,主持法官中經常包括殖民地長官,它的職能是聽取下級法院審理案件中的民事抗訴。高級法院也審理刑事案件。第三級地方法院經手審理殖民地美國的大多數案件。這些地方法院也履行著政府的職能,比如徵募稅收,為市民提供社會活動、經商和討論政治的機會。
這種三級制度經過修改後成為今天各種各樣州法院制度的主要框架。案件在最低一級法院審理,中間一級的受理抗訴案件的法院審查所有審判法庭的抗訴案件,高級法院負責對重要法律問題進行裁決。
隨著殖民地人口的增長,法院判決摘要也變得越來越長。法院應付越來越多的訴訟請求的方法就是使訴訟程式進一步複雜化。當法院提出複雜的程式要求的時候,抗訴案件隨之減少,很多案件被法院駁回。到18世紀早期,隨著受過培訓的律師數量的增加,這種傾向被扭轉過來。
相反,被任命的法官經常是那些沒有受過法律培訓的外行。這種司法知識的缺乏增加了陪審團的重要性。在約翰·彼得·曾格誹謗案(1735)的審理中,陪審團判定被告無罪,儘管法官給出了完全相反的法律要點說明。這有助於確立這樣一條準則:陪審團對法官的法律要點說明要審慎考慮。然而,到18世紀後期,法官在認為陪審團的裁定與證據不符的時候,他們有權命令進行重新審判。今天,在沒有陪審團的審判中——即所謂的板凳審判——法官既要進行法律裁定,又要進行事實裁定。在陪審團審判中,角色被分配開來,陪審團做案件事實判定,而法律判定留給了法官。
到羅訴韋德案(1973)的時候,訴訟當事人使用化名這種做法已經習以為常了,而它最早出現是在17世紀80年代的後期,即“約翰·多爾”和“理察·羅”的案子中。隱去原告和被告的真實姓名意味著在案件審理的過程中,將按照案件的具體性質進行裁定,而不依據當事雙方的影響和關係。這種模式給很多被告以信心,他們希望能避免草率和不公的裁決。
美國憲法第三條以及第一部法官法(1789)確立了聯邦法院的三層制度,它大致是以當時各州運行的三方參與制度為藍本的。下面的兩層,包括審判和抗訴法院,是在地區範圍內組織的,前者在數量上大大超過後者。地方法院過去是而且今天依然是審判法院,由單一的地區法官操縱。巡迴法院,即現在的聯邦抗訴法院,當時雇用由三個法官組成的陪審團,跟今天一樣。儘管在當時巡迴法院主要是審判法院,而今天抗訴巡迴法院致力於複審地方法院的裁決。最高法院當時主要——現在幾乎是無一例外地——致力於複審低級抗訴法院的裁定,無論是聯邦的,還是各州的,然而,眾所周知,最高法院對各州主權給予了充分的尊重。例如,在巴克訴貝爾案(1927)中,最高法院認為維吉尼亞法令批准18歲的卡莉·巴克被迫絕育是符合憲法的,因為她的媽媽生來弱智。而且包括九名法官坐庭。
憲法制定者們所承認的聯邦主義原則準許各州保留重要的權利。聯邦政府負責國家事務,比如外交關係以及州與州之間的往來,而各州保留著它們傳統的治安權力,比如管理公共健康、安全和道德規範。隨著20世紀後半期對公民權利的強調,各州很多調整道德規範的企圖被推翻。例如,在格里森沃爾德訴康乃狄克州(1964)案件中,最高法院發現該州(1879)的一條禁止使用或散發避孕工具的規定是違背憲法的。儘管法官在《權利法案》中沒有找到廢除這條規定的根據,但他們把新解釋的一項權利即隱私權作為他們裁定的依據。在羅訴韋德案中,這項權利得到了進一步拓展。結果,整個19世紀,法律很多領域的發展是由各州自己的立法機構和法院承擔的。直至今天,各州在契約法、刑法、侵權行為和非刑事侵害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
相反,聯邦法院的司法權,或者審理和裁判權,僅限於審理不同州之間的公民之間的案件、海事案件、以及聯邦法律管轄下的案件。第三種權力帶來了聯邦習慣法原則的發展,包括解釋憲法和法律條文的權力,以及推翻它們的權力,正如馬伯利訴麥迪遜案一樣,它確立了司法複審的原則。這是內戰前的唯一特例,在更加臭名昭著的斯科特訴桑福德(1856)案中,最高法院廢除了一項聯邦法律。法院發現《密蘇里和約》是違背憲法的,原告是一個奴隸,而不是一個公民。當聯邦法院審理不同州之間公民的案件的時候,即我們所說的差異案件,它們必須運用根本性的法律,使每一個州都能從最後結果中獲得最大的利益。
每個州法院都有它自己的一套程式規則。分別從1938年和1945年開始,聯邦法院開始遵循他們自己的民事和刑事程式規則,它與各州法院遵循的程式大相逕庭。
程式規則管理的不僅是審判本身,也管理著所有前導的有重要法律意義的事件。例如,它們可能管理著民事案件中原告提起訴訟的形式,即我們習慣上所說的起訴,它為立案奠定基礎。這些規則通常規定被告必須以正式形式對原告指控的時間做出答覆。這些規則眾多而複雜,它們必須有效安排訴訟律師武器庫中眾多的法律武器,其中大多數要在審判開始前使用。實際上,大多數訴訟當事人沒有走進法庭內部。相反,他們的時間都用在與對方談判和起草訴訟請求上面了(通常,如果對方由律師代理,那就要通過他的律師進行談判民事案件中的雙方——甚至是在一些刑事案件中——可以為他們自己進行辯護。儘管如此,在吉迪恩訴韋恩懷特案(1963)中,最高法院規定在任何一個重罪審判中,每個被告有權為自己辯護,如果被告沒錢請自己的律師,國家就要提供。)。訴訟申請可以是下面的內容:潛在證人的審判前證據,以及檔案和信息的交換,這為審判拉開了序幕。簡而言之,就是“透露”(指當事人必須透露事實真相等內容——譯者注)。希望對方的案子在審判前被駁回也可以是訴訟請求的一個內容。
透露的目的是篩除那些在審判中可能沒有價值的證據,比如不可靠證人的證明。同時,也是為了查明一些實際有爭議的問題,以免任何一方毫無防備——比如出人意料的證據等情況。起碼的要求是雙方在審判開始前都應該掌握與案件相關的所有信息,但通過透露揭露事實還是很晚近的發明。隨著《聯邦民事程式規則》的頒行,透露才成為訴訟的一個重要的部分。它也成為當今關於訴訟延遲和花費這一問題進行爭論的核心內容。
透露一旦完成,雙方訴訟請求的裁定一經做出,就要採取更多的預防措施以保證審判順利進行。原告和被告雙方的辯護律師向法庭提交審判前的目錄草稿。該目錄包括自己一方要傳喚的所有證人的名單,以及己方要在法庭展示的檔案記錄或物證。接下來,如果案件是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中的原告方已經選擇邀請陪審團的話,雙方就要選擇陪審團,這個選擇過程稱為(考察證人或陪審員是否合適的)預先審查。而且,尤其是在近些年裡,預先審查已經成為審判的一個重要階段,因為每一個辯護律師都會用盡機謀使陪審團同情自己的一方。
在一些刑事案件中,大陪審團開始審案。大陪審團傳統上由23個陪審員組成(與審判中6—12人組成的陪審團不同),它的目的是判斷原告提供的事實和指控是否可以作為起訴和最終審判被告的正當理由。其他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可以拿到審判前到庭的其他形式的只聽取訴訟證據的陪審團面前。例如,儘管電影明星拉娜·特納的14歲女兒謝利爾·克里斯蒂納·克萊恩因為年齡小自己沒有出面,但她仍然成為1958年一個驗屍官陪審團就其母親情人被殺事件進行訊問調查的對象。因為驗屍官陪審團提交了一個合理殺人的裁定,對克萊恩的犯罪指控被撤回。
憲法《第六修正案》保證被指控的一方有選擇自己同輩人做陪審團的權利,這個觀念跟習慣法本身一樣古老。《第六修正案》還保證被指控的一方被不偏不倚的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因此,在刑事案件審判中,陪審團的選擇更為嚴格。儘管預先審查總是使得雙方律師因為某種理由或者根本沒有理由否定預選的陪審員名單(稱之為強制反對),但《第六修正案》規定這個過程應該最後產生一個代表社會公正且不歧視任何階層任何人的陪審團。關於潛在陪審團的種族平衡問題的爭論可能是雙方策略的核心,正如在1968年黑豹黨人休伊·牛頓謀殺案審判過程中被告律師的質疑一樣。如果案件受到過多的外界干擾,法庭可以採取特別的措施保證陪審團的公正:封閉陪審團,推遲審判,甚至可以更換地點,正如1967年對殺人犯理察·斯派克的審判一樣。
審判從雙方律師的公開辯論開始,首先是原告辯護律師闡述他的觀點——在大多數刑事案件中,律師通常是官方的,比如地方檢察官。(在原告陳述完畢之後,被告可以保留公開辯論的權利。)辯論可以使法官和陪審團對雙方提出的證據以及雙方各自對該案件的看法有一個全面的了解。接著,原告辯護律師進行他的陳述。首先是對原告提出的證人進行直接質詢,證人可以是所謂的專家證人,即不能對案件提出事實證據,但可以對相關的專業知識提供證明的證人。在直接質詢中,同時出示書面或具體的證據。每一方只允許向自己一方的證人公開提問,除非證明那個證人懷有敵意,遇到這種情況,就要向他提出一些誘導性問題,甚至是反詰。
反詰一般是由對方辯護律師進行的,他可以在證人退庭前向每一個證人提問。反詰的目的是對證人提出質疑或者使已經明了的事實更加有利於該律師所代表的一方。如果反詰得出的證據不利於進行陳述的一方,這一方可以通過對證人的再直接調查來駁回或澄清前面的證據。
當原告方列舉了所有的證據之後,被告方按照同樣的過程進行陳述。當雙方都對法官或法官和陪審團陳述完畢之後,先由原告律師,再由被告律師進行總結陳述,總結得出當事人的結論。如果是陪審團進行審理,法官會根據相應的法律對陪審員做出指示,包括哪一方有舉證責任,以及這種責任的尺度是什麼。舉證責任方要想取勝必須符合舉證的三個標準。大多數民事案件使用“證據優勢”標準,意思是說調查員必須保證所列事實一定要真實。有些民事案件,比如那些包含欺詐的案件,要求清楚可靠的證據,使事實確鑿無誤。最高標準適用於刑事案件,被告的罪行不能有一點讓人懷疑的地方。
陪審團有時候要經過幾個星期的審慎考慮。法官作為法律和事實的發現者有時候要仔細斟酌,有時候則要在離開法官席的時候當即做出裁定。如果案件屬於刑事案件,裁定必須是一致的。要經過相當長時間法庭才最後宣布它的裁定,並進行判決。
書面證據的採用受正式的規則的制約。儘管不是所有的州都制定了他們自己的證據規則,但1975年生效的《聯邦證據規則》在大多數聯邦法院對民事和刑事案件起著制約作用。正如我們所猜測的,刑事案件有特別的規則。例如,如果在一個刑事案件中,某個州希望採用某個被告的供狀,法院必須做一個庭外調查,並聽取陪審團的意見(這也叫預先審查)。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判斷供狀是否是在保證被告米蘭達權利該權利因標誌性案件米蘭達訴亞利桑那(1967)案而得名。該法案規定在犯罪嫌疑人被捕之時,要告知他們有保持沉默的權利,讓他們知道他們所說的任何話都可能被利用為攻擊他們的證據,而且,如果他們沒錢請律師,國家應為他們提供律師。的基礎上自願出具的,是不是符合憲法。
律師可以在審判中提供任何新的他們認為可以對當事人有所幫助的證據——主要是人證,他們對手的任務是反對並阻止這些證據被採納,最常見的反對理由是關聯性、傳聞或拒絕泄露內情權。
關聯性是指提出的證據與所要支持的觀點之間的聯繫。相關的證據,無論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必須能證明某個事實對案件而言是重要的。如果不公和偏見的危險超過了相關證據提供證明的價值,或者使案件更加混亂不清,或者誤導了陪審團,這些證據可以被拒絕。 間接證據的說服力以及造成損害的可能性在1955年伯頓·阿伯特綁架和謀殺案中得到了很好的說明,被告被判毒死在死刑毒氣室,主要是因為儘管缺乏任何實際的證據,地方檢察官設法提供了受害者的沒有洗過的內衣,它的樣子和氣味給陪審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相關證據,比如可以確定證人的不負責任的證言會引起紛爭的時候,他提供的證據也不會被接受。
反對傳聞原則也許是最重要的——當然也是最複雜的——即證據的排他原則。《聯邦準則》把傳聞界定為“一種證明所說事實真實可信的敘述,而不是聲明人在審判或聽證中提供的證明”。換句話說,證人所提供的關於他人所說的、所寫的或者非口頭表達內容的證據不能作為所交流內容的可信的證據。之所以堅持反對傳聞原則,是因為證人的可信度是確定他的證言真實與否的關鍵。如果對方不能反詰傳達訊息的人,如果陪審團不能仔細審查證人的行為,就沒有足夠的根據判斷證人陳述的準確度。刑事案件中出現的一個特例問題就是,《第六修正案》授予被指控的一方質詢或反詰所有對自己不利的證人的權利。
傳聞原則有很多特例,通常根據陳述的可信程度以及作為特例的必要性而定。例如,證人敘述一個人的臨終遺言的時候,他的證據通常是被接受的,根據是一個將死之人不會因為撒謊而得到任何好處,如果你對這一點有疑問,你只需要看看1960年芬奇-特里高夫案就清楚了。其中一個被指控為殺人犯的犯罪嫌疑人得到允許在法庭上大聲宣讀他妻子臨終時為自己自殺所做的懺悔。也因為這是在講述人死後留下來的唯一證詞。正像我們看到的,刑事案中的特例給被告——他的生命和自由繫於一髮——提供例外保護的特例更少。但情況也不盡然。州法律中有一個特例就是允許採納一個共謀者揭發其他共謀者所作的陳述,即使他的陳述是在所有共謀者都已在押的情況下所做的。這被認為是符合憲法的,即使通常的原則是這個共謀者的特例不適用於任何拘押後的陳述。
阻止接受新證據的第三個理由是拒絕泄露內情權,這個原則適用於發生在法定權利背景下,或者是其他私密關係中,比如夫妻之間,牧師和他的懺悔者之間,醫生和病人之間。
當然憲法《第五修正案》也規定了一個人拒絕做不利於自己的證明的權利,即拒絕自我牽連的權利。
審判法院作出裁定或刑事案件宣判之後的一段時間為當事人提出抗訴的時間。在刑事案件中,裁定或判決可以被抗訴。在1951年尤利斯和艾絲爾·羅森伯格間諜案審判之後,判決執行拖延了兩年的時間,因為他們就審判的過程和刑罰的嚴苛都進行了抗訴。
在聯邦和大多數州的司法制度中,有兩個潛在的抗訴階段:從審判法院到中級受理抗訴法院,然後到高級法院。敗訴方有向中級抗訴法院提出抗訴的自由權利,而在大多數高級法院中,聽取抗訴通常要慎重斟酌決定。(抗訴通常要有訴狀並獲取有調取案卷令狀後才能到達高級法院。)
在習慣法發展的早期階段,無論在英國還是美國,法院被分成兩種類型: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普通法院根據已經被接受的習慣法原則進行裁決,但侵害行為發生而普通法院沒有現成的補救措施的時候,衡平法院可以根據公平的一般法則解決這些問題。在衡平法院抗訴,要提交事實和法律,對之進行複議和重審。但是,現在,兩種法院已經融合在了一起。抗訴尋求的結果是推翻低一級法院的裁決或者進行重新審理,其理由幾乎無一例外的是法律的運用不當——比如法官對陪審團所指示的本案件所採用的法律——或者是程式錯誤。
刑事和民事案件抗訴一般遵循同樣的軌跡。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差別在於雙重危險處境上面。只在刑事案件中存在的雙重危險處境原則是習慣法里根本的東西,但在《第五修正案》中有特例,它指出“任何人不能因為同樣的罪行被兩次置於生命或肢體的危險處境中。”這個原則在聯邦和各州之間得到推行。它防止了第二次審判,除非第一次是無效審判——在裁定前即宣布無效的審判,通常是因為陪審團陷入了僵局——或者被告對判罪進行抗訴。例如,1982年克勞斯·范·布羅被定罪企圖謀殺妻子之後,他卻在1985年的二審當中卸掉了所有罪責。警官、被告們並不都像范·布羅那樣幸運,但是,雙重危險處境也防止了雙重懲罰,甚至使得任何在重審中加重刑罰的要求須經進一步的司法調查。在美國聯邦制度下,州和國家政府被認為是”獨立自主”的。因此,各自都可以在不踐踏“禁止雙重危險處境原則”的前提下根據不同的法律因為同一個罪行對被告進行審判。這個原則使得聯邦政府在1993年以踐踏羅得尼·金公民權罪審判了四個洛杉磯警官,即使被告在前一年在州法院過度使用暴力的指控中被判無罪。
可以說沒有哪個律師對司法實踐中的所有方面都了如指掌。抗訴比審判需要更高超的辯護技巧。通常,審判律師的技巧主要在於對人性的敏銳的觀察。比如,在三件套裙案件(1911)中,被告律師麥克斯·斯杜爾能在諸多分歧中得到一個無罪的裁決,是因為他懂得陪審團的心理。
有兩個工廠主因他們的146名工人死於火災而被送上被告席,理由是工人們工作的紐約城的血汗工廠按照被告的命令被上了鎖。表面看起來兩個被告的案子不值得同情,但是,斯杜爾能夠通過訴諸他們的直覺戰勝了陪審團的感情。斯杜爾有重要的控方證人——一個在火災中倖存的年輕姑娘,她把她的證詞重複了三遍。前兩遍一模一樣,而第三遍她改變了一個字。斯杜爾確信陪審團已經注意到證人是經過排練的,所以他贏得了這個案子。
其他一些審判律師——丹尼爾·韋伯斯特一下子跳入我的腦海——不是在他們的質詢技巧上獲勝的,而是因為他們雄辯的口才。但高超的辯護技巧和重大的案子結合起來的時候,就產生了令人難忘的審判。儘管1925年的司考普斯“猴子案”——即進化論學說,有重要的社會意義,但使該案件令人難忘的原因是克拉倫斯·達羅對原教旨主義政客威廉·詹寧斯·布賴恩——他是作為《聖經》專家做被告證人的——的機智的質詢,這是一種反傳統的策略,前提是布賴恩也做原告的辯護律師。
司考普斯案被改編成了戲劇,後來又被拍成了電影,它們用了同一個名字《遺傳風波》。其他案件,比如1943年埃羅爾·弗萊恩強姦案,它們之所以有名,是因為它們把名人和醜聞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有些案件臭名昭著,是因為公眾認為不公平,比如1979年丹·懷特案,被告被判過失殺人而不是謀殺——部分原因在於不按常規行事的國防部,它認為懷特食用垃圾食品才是真正的兇手。
但也有些案件之所以出名,不是因為當事人有名,或者是誨淫的事實,或者是高超的技巧。正如在這篇文章開頭我寫的那樣,是因為它的公眾性。引人注目是大案要案的一個特徵,但或許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案子,對我們的人民最具深遠意義且影響最為深刻的是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1954)。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最後由最高法院裁決,勝訴方的辯護律師瑟古德·馬歇爾後來成了最高法院法官。這個案子的核心問題是,一個普通百姓希望她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權利得到認可。由於推翻了“分離但平等”這個一直以來使我們社會分離合法化的原則,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點燃了一場社會革命,它改變了我們每個人的生活。
麗莎·帕多克
前言
古代
亞西彼德審判:公元前415年
蘇格拉底審判:公元前399年
加伊烏斯·維瑞斯審判:公元前70年
拿撒勒的耶穌的審判:公元33年
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
貞德審判:1431年
馬丁·路德審判:1521年
托馬斯·莫爾審判:1535年
麥可·斯文特斯審判:1553年
馬丁·蓋爾審判:1560年
蘇格蘭女王瑪麗審判:1586年
喬達諾·布魯諾審判:1592年和1600年
17世紀
沃爾特·雷利審判:1603年和1618年
火藥陰謀審判:1606年
伽利萊奧·伽利略審判:1633年
查理一世審判:1649年
18世紀
約翰·賓軍事法庭審判:1756年-1757年
仁愛號譁變者軍事審判:1792年
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托瓦內特審判:1792年和1793年
夏洛特·科黛審判:1793年
19世紀
丹尼爾·姆納坦審判:1843年
丹尼爾·奧康奈爾審判:1844年
威廉姆·柯萬審判:1852年
惠斯勒與羅斯金案:1878年
凱利黨審判:1880年
亞歷山大二世刺殺案審判:1881年
阿德萊德·巴特利特審判:1886年
弗洛倫斯·梅布里克審判:1889年
奧謝狀告巴涅爾和奧謝案:1890年
威廉姆·戈登-卡明狀告斯坦利·威爾森、伯克利·利維特等人案:1891年
托馬斯·尼爾·克里姆審判:1892年
阿爾弗雷德·德雷富斯審判:1894年和1899年
奧斯卡·王爾德審判:1895年
埃米爾·左拉審判:1898年
1900年-1949年
司蒂尼·莫里森審判:1911年
鐵達尼號質詢案:1912年
亨利埃特·卡約審判:1914年
刺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案審判:1914年
伊迪絲·卡維爾審判:1915年
羅傑·凱斯蒙德審判:1916年
瑪塔·哈里審判:1917年
羅薩·盧森堡謀殺案審判:1919年
穆罕達斯·甘地審判:1922年
赫伯特·阿姆斯壯審判:1922年
希特勒的“啤酒店暴動”審判:1924年
犬養毅遇刺案審判:1933年
議會大廈縱火案審判:1933年
反希特勒陰謀者審判:1944年
亨利·菲利普·貝當和皮埃爾·賴伐審判:1945年
維德昆·吉斯審判:1945年
威廉姆·喬伊斯審判:1945年
紐倫堡審判:1945年-1946年
東京戰爭罪審判:1946年-1948年
穆罕達斯·甘地遇刺案審判:1948年
維克多·克拉夫琴科審判:1949年
1950年-20世紀90年代
喬莫·肯雅塔審判:1952年-1953年)
菲德爾·卡斯楚審判:1953年)
史蒂文·特拉斯科特審判:1959年)
弗朗西斯·加里·鮑爾斯審判:1960年)
波特蘭海軍間諜團伙審判:1961年)
阿道夫·艾希曼審判:1961年)
奧巴基米·阿沃洛沃審判:1962年)
戴高樂刺殺陰謀審判:1963年)
納爾遜·曼德拉審判:1963年-1964年)
雷吉斯·德布雷審判:1967年)
巴德爾-邁因霍夫審判:1975年-1977年
吉爾福德四人審判:1975年)
瓦茨拉夫·哈韋爾審判:1977年-1989年)
安納托利·斯查蘭斯基和亞歷山大·金茨堡審判:1978年
保羅·瓦克瓦羅·伊凱審判:1981年)
伊莎貝爾·庇隆審判:1981年)
穆罕默德·阿里·阿賈審判:1981年和1985年-1986年
紅色旅審判:1982年-1983年
林迪和麥可·張伯倫審判:1982年
阿根廷的骯髒戰爭審判:1985年
沙佩維爾六人審判:1985年
英迪拉·甘地刺殺案審判:1985年-1986年
西西里黑手黨成員審判:1986年-1987年
彼得·賴特:《捕諜者》審判:1986年-1988年
讓-貝德爾·博卡薩審判:1986年-1987年
約翰·丹真朱克審判:1987年-1988年
克勞斯·巴比審判:1987年)
貝魯特劫機案審判:1988年-1989年
卡爾·古斯塔夫·克里斯特·彼得松審判:1989年
尼古拉和埃列娜·齊奧塞斯庫審判:1989年
南非警察殺人小隊誹謗罪審判:1990年-1991年
戴維·米爾加德聽證:1992年
休·羅德里格斯抗訴:1993年
卡拉·霍穆爾卡和保羅·伯納多審判:1993年和1995年
羅伯特·湯普森和喬恩·維尼堡審判:1993年
羅斯瑪麗·韋斯特審判:1995年
海員馬庫斯·D?吉爾、海軍一等兵羅德里克·哈普、海軍一等兵肯德里克·M?·勒
岱特審判:1995年-1996年
洛麗·貝倫森審判:1996年
伊加爾·阿米爾審判:1996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