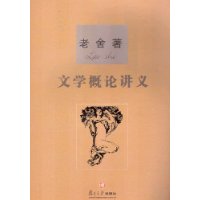 《文學概論講義》
《文學概論講義》內容
第一講 引言
第二講 中國歷代文說(上)
第三講 中國歷代文說(下)
第四講 文學的特質
第五講 文學的創造
第六講 文學的起源
第七講 文學的風格
第八講 詩與散文的分別
第九講 文學的形式
第十講 文學的傾向(上)
第十一講 文學的傾向(下)
第十二講 文學的批評
第十三講 詩
第十四講 戲劇
第十五講 小說
文章節選
在第一講里,我們略指出中國文士論文的錯誤,是橫著擺列數條,沒管它們在歷史上的先後。現在我們再豎著看一看,把古今的重要文說略微討論一下。
先秦文論:文學,不論中外,發達最早的是詩歌。象《詩序》里的“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那樣心有所感,發為歌詠,是在有文字之先,已有的事實。那么,我們先拿《詩經》來研究一下,似乎是當然的手續。《詩經》,據說是孔子刪定的,這個傳說的可靠與否,我們且不去管;孔子對於《詩經》很喜歡引用與談論是個事實。
《詩》中的《風》本是“出於里巷歌謠之作,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也。”(朱熹)它們的文學價值也就在這裡。可是孔子——一位注重禮樂、好談政治的實利哲學家——對於《詩》的文學價值是不大注意的;他始終是說怎樣利用它。他用“《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篇》)定了讀《詩》的方法;於是惹起後世注《詩》的人們對於《詩》的誤解:“刺美風化”是他們替“思無邪”作辨證的工夫;對於《詩》本身的文學價值幾乎完全忘卻。這是在思想方面,他已把文學與道德攙合起來立論。再看他怎從其他方面利用《詩》:
“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篇》)《詩》的用處是幫助修辭的。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禮記·經解篇》)這是以詩為政治的工具。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篇》)《詩》不但可以教給人們以事父事君之道,且可以當動植物辭典用!
這樣,孔子既以《詩》為政治教育的工具,為一本有趣的教科書,所以他引用詩句時,也不大管詩句的真意,而是曲為比附,以達己意,正如古希臘詭辯家的利用荷馬。鈴木虎雄說得好:
“孔子當解釋詩,對於詩的原意特別注重把來安上一種政教上的特別的意義來套用。……例如述到逸詩:‘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必評論說:‘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論語·子罕篇》)原篇雖是說男女相思,因居室遠而相背的。對於這下一轉語,可說是相思底程度不夠,倘若真相思便沒有所謂遠這一回事的,恰如利用所謂:‘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篇》)的意義一樣。政教下的談話成了乾燥無味(之談,而)①由此得救了。又在《大學》里引《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商頌·玄鳥》)《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小雅·魚藻之什緡蠻》)也說:‘於止,知其所知,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大學》)掇拾‘止’字以利用《大學》的‘止於至善。’……子夏問到《詩》里所說:‘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怎樣解釋,孔子答以:‘繪事後素。’子夏遂說道:‘禮後乎?’(《論語·八佾篇》)孔子又說子夏是‘可與言詩’的。甚至稱讚為‘起予者商也。’但這種問答詩底原意已被遺卻,只是借詩以作為自己講學上的說話而已。”(《中國古代文藝論史》第一編第四章)
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何等的美!可惜孔子不是個創作家,不是個文學批評家,所以沒有美的欣賞。有孔子這樣引領在前,後世文人自然是忽略了文學本身的欣賞,而去看古文古詩中字字有深意,處處有訓誡,於是文以載道明理便成了他們的信條。
理論構成、意向及其理解的維度
對老舍的《文學概論講義》進行解讀,有三個最為基本的維度,即其一,作為教科書文論,其最為基本的理論構成;其二,其文學觀與理論觀的基本思想來源;其三,作為特定的理論建構,其在當時語境中所獨具的張力機制。
對老舍《文學概論講義》的基本理論構成,我們可以從以下相關側面來進行把握,即其一,文學理論研究的必要性。在這一維度的問題上,老舍明確地指出:“中國沒有藝術論。這使中國一切藝術吃了很大的虧。自然,藝術論永遠不會代藝術解決了一切的問題,但是藝術上的主張與理論,無論是好與壞,總是可以引起對藝術的深厚趣味;足以劃分開藝術的領域,從而給予各種藝術以適當的價值;足以為藝術的各枝對美的、道德的等問題作個通體盤算的討論。”在這裡,老舍所指出的即是藝術本質分析的必要性與有效性,並進而認為:“中國沒有藝術論,所以文學始終沒找著個老家,也沒有一些兄弟姐妹來陪伴著。‘文以載道’是否合理?沒有人能作有根據的駁辯,因為沒有藝術論作後盾。文學這樣的失去根據地,自然便容易被拉去作哲學和倫理的奴僕。”理應指出的是,老舍這裡的“藝術論”,實際上有兩重含義:一是廣義的藝術及其理論,在這一意義上,“文學為藝術之一枝”;二是狹義的理解,指的是藝術的本質分析,亦即對“文學特質”的把握。
其二,老舍《文學概論講義》的文學本質論。在其本質論中,老舍對文學作出了如下的相關界定:“文學的真面目是美的,善於表情的”;“感情,美,想像,(結構,處置,表現)是文學的三大特質”;“創作與自由發展必是並肩而行的”;“藝術品是個性的表現,是美與真理的再生”;“文學與非文學是在乎創造與否”。從以上的相關言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老舍的理論視界中,文學理應是話語形式的、審美的、自由的,因而具有個體創造性。在這裡,老舍確立了自我特定的“純文學”觀,並立足於此來對中國古典文論的流變進行梳理與把握,來對西方的相關理論觀點進行選擇與點評,並進而反對各種各樣的工具論文學觀。這是一方面的問題。另一方面,在老舍看來:“人是社會的動物,藝術家也不能脫離開社會。社會的正義何在?人生的價值何在?藝術家不但是不比別人少一些關切,而是永遠站在人類最前面的;他要從社會中取材,那么,我們就可以相信他的心感決不會比常人遲鈍,他必會提到常人還未見的問題,而且會表現大家要嚷而不知怎樣嚷出的感情。所謂滿足自己不僅是抱著一朵假花落淚,或者是為有閒階級作幾句瞽兒詞,而是要替自然與人生作出些有力的解釋。偏巧社會永遠是不完全的,人生永遠是離不開苦惱的,這便使文人時時刻刻的問人生是什麼?這樣,他不由得便成了預言家。文學是時代的呼聲,正因為文人是要滿足自己;一個不看社會,不看自然,而專作些有韻的句子或平穩的故事的人,根本不是文人;他所得的滿足正如一個不會唱而哼哼的人;哼哼不會使他成個唱家。所謂個性的表現不是把個人一些細小的經驗或低卑的感情寫出來便算文學作品。個性的表現是指著創造說的。個人對自然與人生怎樣的感覺,個人怎樣寫作,這是個性的表現。沒有一個偉大的文人不是自我表現的,也沒有一個偉大的文人不是自我而打動千萬人的熱情的。創造是最純潔高尚的自我活動,自我輳射出的光,能把社會上無謂的紛亂,無意識的生活,都比得太藐小了,太污濁了,從而社會才能認識了自己,才有社會自覺。創造欲是在社會的血脈里緊張著;它是社會永生的唯一的心房。藝術的心是不會死的,它在什麼時代與社會,便替什麼時代與社會說話;文學革命也好,革命文學也好,沒有這顆心總不會有文藝。”在以上精彩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老舍看來,文學不僅是個體情感的自我表現與審美形式的自由創造,同時又是時代性的、社會性的。應該說,在老舍的文學本質論中包含著豐富的藝術辯證法,這種有關藝術本質的辯證理解,直到21世紀的當下,仍具有其啟示意義。
其三,老舍《文學概論講義》的藝術辯證法觀念。老舍的藝術辯證法思想在《文學概論講義》中體現在各個相關側面,在這裡,我們可以通過其對文學內容與形式之間關係的辯證解讀為例來進行辨析,進而得到相應的理解。老舍指出:“形式與內容的關係也是由討論整個的藝術才能提出的,因為在討論圖畫雕刻與建築之美的時候,形式問題是要首先解決的。有了形式問題的討論,形式與內容的關係自然便出來了。”通觀《文學概論講義》,我們可以看到,老舍十分重視文學形式的特質及其功能,並以審美形式為前提、為中心來把握文學的內容與形式及其關係。亦正基於此,老舍才指出:“在一切美中必有個形式,這個形式永遠是心感的表現。無表現力的感情,無形式之美的心境,是野蠻的;打磨光滑而無情感的韻語是藝術的渣滓!形式之美離了活力便不存在。藝術是以形式表現精神的,但拿什麼形式來表現?是憑美的怎樣與心相感應。形式與內容是分不開的。形式成為死板的格式便無精力,精神找不到形式不能成為藝術的表現。”以上的論述把握住了藝術形式與其內容之關係形態的審美規定性,比之左翼文論的簡單化理解,無疑要深刻得多。在這裡理應指出的是,老舍有關文學內容與形式關係問題的論述雖充滿著辯證法,但其相關理論卻是不完備的,分析也不夠充分,並且其“文學形式”的概念近於“文體樣式”或“文學體裁”的概念。應該說,老舍是以形式作為立足點來探討藝術內容與形式之間的辯證關係的,亦正是在這一點上,老舍的文藝觀與當時的左翼文學論分界開來。
其四,作為教科書文論,老舍在《文學概論講義》中所確立的基本理論框架。老舍對“文學概論”亦即教科書文論的特質已有較為全面的了解,當其時,日本、蘇聯、西歐的相關著作多有翻譯,這些著作對老舍《文學概論講義》的編寫無疑是有影響的,據統計,在《文學概論講義》中,老舍“直接引用了一百四十位古今中外學者、作家的論述、作品和觀點”,其中一部分即是相關的教科書文論。但老舍在文論教材的編寫中,還是有自己的特色與匠心的,《文學概論講義》共十五講,大致可分為以下相關的構成部分,亦即其一,引言(第一講),文學概論課導言。其二,“特質論”或稱本質論(第二、三、四講),探討文學的本質究竟是什麼,為了避免抽象的邏輯論說,以“兩講”來介紹中國古代文論的相關觀點,借相關辨析而提出自我對文學的基本界定。其三,創作論(第五講),分析“文學創造”的本質及其機制。如老舍即認為“文學的成功以怎樣寫出為主,說什麼是次要的”;這無疑是切合文學創作的基本規定性的。其四,思潮-發展論(第六、十、十一講),於其中,對“流派”、思潮與“傾向”概念的辨析是值得注意的。在《文學概論講義》中,老舍並未設專章來講述“文學發展”、“文學史理論”等方面的問題,但其中“文學的起源”(第六講)、“文學的傾向”兩“講”(上、下,第十、十一講)以及“中國歷代文論”兩“講”(上、下,第二、三講)等,其中即涉及到豐富的文學史哲學思想與對中西文學史乃至理論批評史的精當把握與解說,如認為文學形式在文學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文學形式的研究足以有助於看明文學的進展”;文學的發展受到時代的規定而又具有自身的相對獨立性,“作家的個性是重要的,但是他不能脫離他的時代;時代的色彩在他的作品中是不自覺而然的;有時候是不由他不如此的”;從“歷史的觀點看詩藝,它的發展也不只是機械的形體變遷;時代的感情,思想,與事實或者是詩藝變遷更大的原動力。”這些相關論述對於我們建構較為完備的文學史哲學,還是有其啟示意義的。老舍對中國古代文學史之流變與演革的把握,也有其獨特的觀點,亦即把中國古代的“文學傾向”分作三個大潮,即“正潮”(秦漢以前)、“退潮”(自秦漢到清末)與“暗潮”(俗文學及其發展)。另外,對西方文學史現象,如文藝復興與新古典主義、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新浪漫主義與浪漫主義等所作出的比較與點評,亦多有精彩之處。其五,風格-形式-形態論亦即作品論(第七、八、九、十三、十四、十五講),在這一維度中,既涉及到個體風格的創造及其類型,涉及到文學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問題,也涉及到文學作品的形態類型問題。於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老舍對詩與散文的分界、對“律動”的深層解說與作品形態類型學的“四分法”。其六,批評論。老舍的批評形態類型論採納的是莫爾頓(R·G·Moulton)的觀點,亦即將文學批評劃分為理論的批評、歸納的批評、判斷的批評與主觀的批評,並基於自我基本的批評觀念而給予了新的解釋。在我看來,老舍批評論中所提出的“同情的理解”頗具創新性與現實針對性。通過以上的歸納與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老舍的《文學概論講義》基本體現出20世紀中國教科書文論之建制及其規範化的趨向。
《文學概論講義》文學觀與理論批評觀的基本思想來源是中國古代的“情志派”尤其是西方的相關美學思想與文藝理論觀點。於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學理論家廚川白村的文藝觀對老舍早期文藝思想的影響。當然,如上的吸納與借鑑是以老舍自身的創作實踐及其體驗、經驗與感悟作為基本機制的。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從本質-本體論的意義上言之,老舍在《文學概論講義》中所確立的是重視情感-個性表現與形式創造的審美本體論文學理論。從理論思潮基本取向的意義上言之,老舍在《文學概論講義》中所確立的是文化自由主義的文學理論,進而與文化激進主義、文化保守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分界開來。亦正基於如上的規定性,有人才作出了如下的評價:“進入30年代之後,隨著‘文藝戰’的展開,一方面以文學為理論戰場的普羅文學的號召激動一時,另一方面,維護文學獨立,甚至自足價值的言論也得以加強。老舍在1930至1934年任教於齊魯大學時的講義《文學概論講義》就特別體現了維護文學獨立價值的傾向。”從理論形態的意義上言之,老舍的《文學概論講義》屬於教科書文論,但基於其理論主體的基本特性與《文學概論講義》的實際構成,其實質上是教科書文論與體悟性文論的整合體。
歷史意義及其啟示
老舍《文學概論講義》所具有的意義及其啟示無疑是多方面的,於其中,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是以下相關側面,即其一,《文學概論講義》對於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新傳統”之建構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及其啟示;其二,其現實針對性與解說力;其三,對理論建構及其功能的重視與強調;其四,其活潑、簡捷並基於自我創作體驗與感悟的教科書文論形式。
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近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包括學術性文論、教科書文論等)尚處於初創階段,其必須在中國傳統與西方近現代文學理論的話語表述方式、形態及其體系之間進行選擇,在選擇的基礎上進行意向的確立與理論的整合。這是一種異質向度的整合,其間的關鍵問題即是20世紀中國本土性理論話語與理論表述方式及其意向的確立問題。文言與白話之爭以及白話文地位的確立,無疑為20世紀中國本土性理論話語與理論表述方式的選擇與確立提供了契機與路徑。從一般意義上言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範疇,往往是從對生活現象和創作實際的直覺感悟中總結、提煉出來的,具有具象與抽象結合、體驗與概括結合的特點”;“這種感悟式的批評決非是一些隨意性的印象批評,其背後隱藏著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家的全部文化智慧和審美經驗。中國古代文論的思維方式是建立在認識與感受相統一的基礎上。”與之相比較,西方文論則是邏輯分析式的,概念範疇更為精確,更重視論證嚴密的體系建構。在以上的差異中,“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家,在“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的促動下,他們選擇了以西方文論形態及其表述方式作為基礎而進行創造性整合的理論建構方式,從而確立了現代漢語的理論話語體系。亦正基於此,20世紀中國的文學理論,不僅不同於中國古代的傳統文論,也不同於西方文論,在某種意義上乃至可以說,20世紀中國文論形成了自身的“新傳統”。無疑,老舍的《文學概論講義》是這一新傳統中的一部分,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進而言之,我們只有立足於20世紀中國文論的新傳統及其建構,才能在真正意義上對老舍的《文學概論講義》作出歷史定位和具有歷史性的解釋。
在《文學概論講義》中,老舍雖以極大的篇幅點評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但其理論話語及其體系卻不是中國古典式的;在30年代的中國,俄蘇文化思想與文學理論批評對中國文化思想界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乃至在文學界與理論批評界出現了向“左”轉與“蘇化”的傾向,但老舍的理論話語及其體系卻不是“蘇式”的、“左傾”的,而是選擇並確立了一種新的理論形態,雖然這種理論形態之建構明顯地接受了來自西方的影響。應該說,老舍的《文學概論講義》不管其是否自覺,事實上,其參與了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新傳統”的建構。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到40年代末,中國教科書文論在自身的發展中,一般選擇這樣四種較有代表性的路徑,即其一,直接採納中國古代文論;其二,直接搬用西方文論,有的甚至直接編譯歐美、日本等國家的相關文學理論著述作為教材;其三,直接搬用俄蘇文論;其四,基於主體自我的理解、學養與觀念而對中西、古今文論進行創造性整合。歷史的考察表明,也正是第四種路徑或稱文論建構的方式促動著20世紀中國文論新傳統的生成與發展。應該說,有關20世紀中國文論“新傳統”的問題,值得人們去加以關注並進行較為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在我看來,這一新傳統並非象有的論者所指出的那樣是“移植”的產物,在這一新傳統中,既存在著移植性質素,也包含著本土性傳統質素的轉換,當然還包含著20世紀中國一系列文學理論批評家的創造性選擇與嘗試。從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老舍的《文學概論講義》在建構本土性文學理論話語及其體系、在促動中國文論新傳統之生成與發展等相關側面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與功能。
應該說,老舍對“革命文學”的這種評價體現出其自由主義的、審美本體論的文藝觀,歷史也確證了這種文藝觀念的張力機制及其解說力。這也表明,教科書文論不能僅僅提供相關的知識與原理,還理應對當下的文學現實有所觀照、有所分析,進而才能提供新知與創見。
在當下的語境中,反本質主義思潮正愈益擴大著自身的影響,一時之間,“文學理論終結”成為一種時髦性的話語與話題。在這一語境之中,老舍在《文學概論講義》中對理論建構及其功能的重視與強調,無疑是值得注意的。對於20世紀中國文學及其理論批評史的研究而言,對現代漢語的詩性(審美)品格與思辯(理論)品格的思考與探討,無疑是最具基礎性的一項工作,這一工作對於當下的文學理論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亦正基於此,在當下文學理論的重建中,有人既提出“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問題,也提出“西方文論的中國化”問題,指出:“西方文論話語需要與中國傳統話語、中國獨特的言說方式相結合”。應該說,“西方文論中國化”並非是一個新的命題,事實上,在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發展的過程中,許多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皆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過這項工作,如老舍的《文學概論講義》等。在這裡,我們所理應關注並進行系統考察的是,20世紀中國不同的理論主體、流派與形態各自是以何為基點、以何種方式來對西方文論進行“創造性轉化”的,其經驗教訓何在,如此等等。於其中,老舍的《文學概論講義》無疑提供了一個可供分析的特定範例。進而言之,對於當下建構多元化、個性化而又灌注豐厚的啟蒙意識與人文理念的教科書文論來說,老舍的《文學概論講義》也具有其獨特的啟示性。
總之,在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的教科書文論尚未體制化、模態化,其體例尚未定型,各家各派的教科書文論雖有共同之處,但其差異與區辨卻是最為明顯和主要的。於其中,老舍的《文學概論講義》,一方面體現出了教科書文論與體悟性文論相整合的特質;另一方面,其體例更為接近20世紀中國教科書文論的主導性範式,因而是值得重視並加以進一步研究的。
作者介紹
 老舍
老舍老舍(1899.2.3-1966.8.24),現代作家,原名舒慶春,字舍予,滿族正紅旗人,北京人,父親是一名滿族的護軍,陣亡在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城的時候。老舍是他在小說《老張的哲學》中使用的筆名。他的筆名還有絜青、絜予、非我、鴻來等。中國現代小說家、戲劇家、著名作家,曾任國小校長、中學教員、大學教授。
老舍有文學語言大師的稱號。其中包括三百多萬字的小說,四十二部戲劇,約三百首舊體詩等。他的作品多為悲劇,作品的語言以北京方言為主,風格幽默。他的代表作是小說《駱駝祥子》和話劇《茶館》,這兩部作品現已列入中國初高中語文必讀書目,和大學中文專業必讀書目。《茶館》也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高中華文文學必修的作品。舒乙等人認為老舍的作品中反映了他對滿族的隱含的、深沉的、難以言語的真摯的感情。
老舍以長篇小說和劇作著稱於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於市民生活,為中國現代文學開拓了重要的題材領域。他所描寫的自然風光、世態人情、習俗時尚,運用的民眾口語,都呈現出濃郁的“京味”。優秀長篇小說《駱駝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寫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說構思精緻,取材較為寬廣,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斷魂槍》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他的作品已被譯成20餘種文字出版,以具有獨特的幽默風格和濃郁的民族色彩,以及從內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賞而贏得了廣大的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