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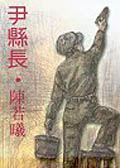 《尹縣長》
《尹縣長》書籍作者:Chen Jo-Shi 陳若曦
圖書出版社:ein Ullstein buch
圖書品相:8.5成品相
庫 存 量:1 本
圖書售價:60.00元
圖書類別:文學
圖書標籤:陳若曦 德文原版 尹縣長 Ullstein Chen
上書時間:2009-05-28
出版時間:1982
開本:36開 頁數:256頁
裝訂:平裝 ISBN:3548202047
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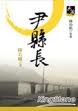 《尹縣長》
《尹縣長》這篇小說寫的是文革初期發生巒陝西興安縣的一個悲劇,在國共內戰中率本部投共的國民黨上校,已為新中國努力工作十多年,連個小小的縣長到“文革”時也罷了。但仍然難逃厄運,終因“歷史問題”而被槍斃,可他臨刑前還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這個冤死者名叫尹飛龍。據作者介紹,原型為一雷姓人物,經歷幾乎末作改動,以血的真實來扔露“文革”謊言。
新版自序
 《尹縣長》
《尹縣長》《尹縣長》在一九八七年出了二十七版後,有十七年之久不曾再版。其間曾想取回自印,卻因為出版社擁有“永久出版”的契約而作罷。
朋友都很訝異: “你不是沒見過世面的人,留學美國,又兩岸三地走透透,怎么會輕易把著作權‘永久’出讓呢?”
說來慚愧,其時人在溫哥華,睽違台灣十多年了。以為家鄉長年戒嚴,管制新聞和出版,出版契約必為既定模式,不可更動。僅有的顧慮是,以後出版選集要抽用部份篇幅恐有不便。在電話中與出版社老闆提起,他表示沒問題,打聲招呼即可。
過兩個月,另一家出版社出版我一本選集,我便選用了《尹縣長》中的兩篇。該出版社寄出契約時,先在電話中表示“契約內容可以按作者意願修改,雙方同意就行。”我這才知道,台灣的出版業相當活潑開放,並無固定契約。
其實出版社肯“永久出版”拙作是好事,苦的是長年不出版,又不讓作者拿回著作權,讓人感到判了無期徒刑似的。這十年來,有些出版社編輯作家作品選,要求從《尹縣長》集中選敝人的代表作,常因轉載費太低而碰壁,也令人備感挫折。
去年九月,出版社突然又印了三百本,旋即傳來老闆遭逢變故的訊息。聽說出版社的繼承人較好商量,我便親自交涉,終以十二萬元代價贖回了著作權。蒙九歌出版社選為“典藏小說”叢書之一,得以校訂再版,欣慰感激就不在話下了。
台灣的民主日漸成熟,海峽兩岸的交流越發密切,約定俗成的用語漸漸融會貫通了。再版的集子因而取消了很多引號,相信讀起來會通順些。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轉眼將滿四十年。隨著時光流逝,人們對這場幾乎革掉中華文化的政治運動,可能記憶淡忘了,甚或全然陌生。無論如何都是可惜的事,因為忽略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悲劇可能一演再演。《尹縣長》寫作不夠完美,卻是那個荒謬、動亂時代的見證。讀者若能從中有所體會,譬如一個民族不追求民主進步並自我反省的話,會有集體瘋狂而墮落、淪亡之虞,作者將會感恩戴德,不虛此生矣。
——二○○五年三月於台北
作者簡介
 作家陳若曦
作家陳若曦陳若曦,本名陳秀美,1938年出生。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寫作系碩士。1960年與白先勇、王文興等創辦《現代文學》雜誌,以寫實小說聞名文壇。1989年創建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1995年返台定居,現在是台灣專欄作家協會副理事長,也是“荒野保護協會”的會員及義工。
她曾獲中山文藝獎、聯合報小說特別獎、吳三連文藝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尹縣長》、《完美丈夫的秘密》等;長篇小說集《突圍》、《遠見》、《慧心蓮》等;散文集《 陳若曦
草原行》、《生活隨筆》等;自傳《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
作品評論
一、作品早期的情感宣洩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中國大陸,陳若曦是有很多想法的。從她早期的作品(注1)「灰眼黑貓」、「欽之舅舅」、「巴里的旅程」…等中,我們可以得知:陳若曦同大多數中國作家一樣,關心中國民間的傳統思想—迷信、生死;關心人生命運的既往開來—反省、解析。而顯現在她的作品裡頭的人物,多半是有缺陷的,而這種缺陷除了是基於人物本身的個性所造成的以外,有更多原因卻是外在的環境影響,如「喬琪」一文中,女主角喬琪是一個懷有憂鬱症,強烈害怕她的生命、自由被佔有的女子,這樣的個性造成了她處世上的偏執和過度偏愛自己,然而她卻擁有一個幾乎把女兒當成生命重心的母親,一個視喬琪為所有物的男友陸成一,在這樣的環境催逼下,喬琪不斷的逃避現實、人群,不斷的自我掙扎,卻終究無法擺脫自身的命運之網,最後只好求助於安眠藥,讓床頭的日光燈替她繼續把夜晚燃燒。這種因為外在環境因素的篇章,在早期陳若曦的作品中不過是一種催化文中主角命運的推手,重要性其實並沒有很大,佔比較重要性地位的,卻是陳若曦在文章中的感情抒發。她在許多早期的作品中所描寫的情感,多是直接而熱切的,如「辛莊」中主角辛莊在洗澡時的一段自憐:『只不過一剎那間,整個人便屈服在這種情感中;淒涼,被遺棄的感覺像蠶兒啃食桑葉一般啃著他的肺臟。』;「灰眼黑貓」一文最後,阿青對於文姐死亡的迷惑:『我常常思索她悲慘而短暫的一生,歸究不出何以她要受到這樣的遭遇。那古老的關於黑貓的傳說,時常閃過我的腦海,我茫然了。她究竟是黑貓或是舊家庭制度的犧牲者呢﹖我不能回答。』……我們是可以很輕易在字裡行間讀出這種激烈的情緒。
二、寫法的丕變而這種激動的情緒宣洩,到了《尹縣長》(注2)中卻突然退居到了文後,代起而出的是另一種冷漠的基調,如「耿爾在北京」裡的主角耿爾,他在現實中的思想色調是灰濛濛的,有一段描述耿爾感嘆自身的孤獨而衍生的話語,很能表達這種情調:『我敢情也老態龍鍾!耿爾想著,往肚裡咽了一口嘆氣。只有七老八十的人想來與我共桌了……想到老,不禁想到自己的年紀。一剎那間,他竟說不出自己的正確歲數。慢著,他心裡默默數起來,一九七四,一九二五……整整四十九。呵,四十九!好像勐吞下一口冰水,一路涼到心底。這邊緣感覺的「九」字,也給他一種里程碑的提示。二九拿博士學位,卅九回中國,現在四十九了。十年了!回來時一個人,現在仍是一個人……。』;再者如「尹縣長」裡的敘述人—旅行者,以一個類似介於中立的旁觀者角色,斷斷續續的拼湊出一生忠於共產黨的老幹部—尹飛龍被黨爭批鬥致死的過程。旅行者見證事件的過程裡,他的同情、憐憫,在陳若曦刻意的筆調下,傷感是微微的、慨嘆是微微的,就連讓旅行者知道尹飛龍慘死的結局,也是在離開小鎮多年以後,聽第三者—小張他弟弟說才知道的。這樣的安排無疑是讓敘述者與事件發生的時空關係更隔了一層,也使得主人翁在這場事件裡的思慮顯得更加冷澹、矇矓。如此異常節制的情感,在文字語言運用的欲語還休,點到為止之下,無可奈何的氣氛幾乎瀰漫在《尹縣長》裡的各個篇章中,讓我們所感覺到的,是在大陸上文革十年而動盪不安的黨政戰爭下,人們過度壓抑情感而扭曲的心理;也是陳若曦對於共產黨在中國所建構的烏托邦夢想,從寄予深厚的期盼到徹底幻滅後,在內心的掙扎矛盾後,再顯現在作品中的成長軌跡。
三、重新提筆寫作從陳若曦在早期作品中的情緒表達濃烈,到《尹縣長》裡的冷漠、內斂,在這樣劇烈變化的文筆風格中,我們知道陳若曦對於當權政府是非常失望的,強烈的不滿在不幸親身見證了泯滅人性、強調「血統論」的階級制度、和動輒得咎的文革後,她本來是放棄寫作的,但為何後來又提起筆了呢?在《尹縣長》這一短篇小說集的前言裡,陳若曦曾「有感」而說過下面這些話:『我在南京住的那幾年,怎麽也沒想到有一天會再提筆寫小說,那時作夢也想不到有離開的一天。誰知天下事難料,有一天竟然人到了香港。……原想不談往事,只將就著打發餘生,然而住在以人為牆的香港,卻倍感寂寞,特別懷念起大陸上的朋友來。……我認識的人自然不多,但每想起他們,就像想起老家台灣的親友,無限的親切。就為抒發這情懷,我又試著拿起筆來。』再次拿起筆來寫小說的陳若曦,當初寫作時的批判性、嘲諷性經過長期的屯居心中,逐漸的走向內化,她不再大剌剌的把一股子熱血霹靂啪啦的全倒出來,而是讓小說裡的人物自己在回憶裡思考亂世中的生命得失,而這種反思是在一種沉潛的狀態下進行的,所以「耿爾在北京」裡的耿爾,每每耿耿於懷逝去的兩段戀情,卻是在已成僵化的日子裡,間斷想起過去的美好;「任秀蘭」、「尹縣長」裡,作者故意由第三者的觀察,連線過往(人物的背景)和現在(事件的進行),進而拼湊出忠貞的老共產黨幹部的死因……,但這並不代表陳若曦對於社會關懷的感情冷卻了,她換了另一種更深層的控訴—間接的嘲諷是要比直接的批判更能震攝人心的,像「尹縣長」裡的小張、「任秀蘭」裡從未露面的主角任秀蘭,在大陸文革裡,他們既是批鬥者,也是被批鬥者,時勢的顛倒變化使得他們都成了政治鬥爭下的犧牲者。
四、時代無奈的申訴然而這種犧牲究竟有什麽意義呢?陳若曦不明著議論,她把自己的感覺從文章中抽離,以一個旁觀者的角色,只在文章上做敘述的工夫,做說故事的敘述,回答這些個難解問題的,是被逼迫的故事人物自己發出來的慨嘆:『為什麽要搞文化革命?』這不但是「尹縣長」裡尹飛龍的疑問,也是《尹縣長》其他篇章裡各個人物的疑問,更是如陳若曦一般愛鄉愛土的中國人最深的疑問,而答桉呢?無解!(或是不知道該怎麽解?)對於這種無法解決的問題,陳若曦讓故事中的人物自己去發表意見,不是從析論不合理之事入筆,這在陳若曦創作早期,或許會讓他們哭鬧一番,但在經歷過風雨之後的陳若曦,深深了解其實人在最痛的時候,是哭不出來的,只有感覺會麻痺,所以她讓小說裡的角色,從敘述他們經過事件的感覺上,使讀者清楚他們的思想變化。「任秀蘭」裡,因為任秀蘭之死,而使陳老師內心受了很深的影響:『我整整病了一星期,每天就是躺在床上,茶飯無思;閉了眼睛後,一件黑乎乎脹彭彭的物體便湧上腦海,使胃裡泛酸作嘔,想一吐為快,偏又吐不出來。慢慢的,我也習慣了,知道這不是生理反應,而是根深柢固地在我心頭的一種感覺,像絞鍊一般,今生怕是解不開了。』甚至遺留下了後遺症:『對於我,就不同了。她的死像一塊鐵投進了我的心海,重重的、愈沉愈深。』
五、傷痕與反應這種痛是很沉的,沉到竟成為大家心上化不去的內傷,而投射在現實生活裡的行為表現,是人人都抱持著一種「只管自己門前雪」的心態:「晶晶的生日」裡,晶晶的媽媽文老師在聽聞喊反動口號的不是自家的小孩時,竟是鬆了一口氣。「查戶口」裡,鄰居們彼此窺探監視,深怕被對方揪住有反動思想或行為的辮子,甚至為了看不慣彭玉蓮的新潮作風,開會組成了一個抓姦小組,這不是擺明著「黨同伐異」嗎?;是「耿爾在北京」裡,耿爾的生活重心只在回憶,對於其他事則是莫不關心的冷漠(或該說是僵化)。心痛到了底就冷在行為上的漠不關心,而行為上的漠不關心卻造就了人際關係的疏離。不管是「晶晶的生日」、「查戶口」中鄰居們的不相熟稔,還是「值夜」、「尹縣長」中主要敘述者的冷眼旁觀,都只顯示出一件事:陳若曦是心痛的,她心痛受文革逼壓下的人民的生活苦悶、心靈禁錮;她無奈於共產領政下,把所有一切推究於「無限上綱」(注3)。所以當她重新提起筆寫下《尹縣長》短篇小說集時,從頭到尾在故事中顯現的色調不是一片淒冷,要不就是老人遲暮之感。希望在哪裡呢?陳若曦把希望都丟到了過去的回憶,從《尹縣長》裡的各個小說有三分之二的篇幅都花在描寫過去的人、事、物上,即可得知。
六、故事的淒冷色調在《尹縣長》小說集裡,故事發生高潮的時間幾乎都發生在夜晚:「晶晶的生日」中,文老師在與隔壁鄰居王阿姨交談時,王阿姨透露出幼稚園小娃兒小紅半夜被審問喊反動口號的事情。之後王阿姨又在晚上告知文老師說她的女兒晶晶也喊反動口號;「值夜」整個故事,在時間發展上,始於晚餐時,終於深夜,全都發生在晚上;「查戶口」裡,居民們在晚上開會商討如何捉姦,同時文老師被指派監視彭玉蓮的任務;「耿爾在北京」中,從黃昏到晚上這一段時間,耿爾都在「東來順」吃涮羊肉,以及回憶與小晴的戀情。後來耿爾到老張家吃年夜飯,重遇小金,又憶起他的第二段情事;「尹縣長」裡,敘述者抵達陝南興安縣當天,晚飯後在尹老家第一次見到尹縣長。第二天晚上,尹縣長來訪,向敘述者尋問文革的意義。敘述者在晚上眼見尹老被迫自白。陳若曦這樣子的時間安排,除了成功的烘托出故事發展的情節氛圍,相對於人物心情起伏的變化,也做到了借景(夜色)抒情的效果—以夜色下的人物思維和活動的描述,來反映一種情緒上的壓抑和悲憤—一如在中國的文革黑暗時期中,百姓們如此長期心緒的抑制造就了整個社會無法舒張的抑鬱感。在夜色的掩映下,沉悶的不僅只是人心(性),更痛的是那些個曾經擁有的美好,現在已逝去的回憶。陳若曦痛啊!怎能不痛呢?所以為了「懷念起大陸上的朋友」,她重新提筆去寫他們在那樣草木皆兵、動輒得咎的環境下,無法說出的苦。用一種置身事外,卻又「提不起,放不下」的筆觸,把她的懷念和悲憫盡數化在字裡行間,即使是批判,也是沉在小說情節的峰迴路轉中,藉小說人物的心和口,間接的去抒發藏在心底那沉之又沉,龐而又龐的疑惑、無奈,在那樣子的一個年代裡,中國人的歷史是黑夜的,被壓抑的百姓生活是恐慌的、是暗夜的。在夜裡,唯一令人振奮的,是過去的回憶;但令人難過的,也是囊昔的流逝。
七、回憶里的美好也因為如此,在陳若曦的《尹縣長》中,故事人物心中最快樂的事多發生在回憶裡,最明顯的例子,像「耿爾在北京」中的耿爾:他在公式化生活裡的唯一消遣是上「東來順」吃涮羊肉,而這習慣是由於過去某段的人事牽成;在吃涮羊肉的這段時間,耿爾又無法克制自己去想起從前的戀情,想起過去那段意氣飛揚,無懼無憂的日子。「回顧」是陳若曦在《尹縣長》中,對於故事情節的推展,最常運用的手法特徵。如果撇開「回顧」這種寫作技巧在小說結構中的運用成效,單就小說氣氛營造上而言,陳若曦的故意使用大量的「回顧」,除了在小說中呈現出時空變化的明顯對比之外,也帶出了「人面桃花」式(注4)的遺憾和傷感。陳若曦對於回憶的美好是有著一份特殊的眷戀,從她在《尹縣長》裡的諸篇小說中,出現許多舊時代的人物,而他們又都具有舊時代的豐沛情感、人情味、善良、敦厚…等特質,如「尹縣長」中敦厚樸實的尹老、「耿爾在北京」裡爽朗豪邁、不失真性的店鋪跑堂老魯,他們的存在不只代表了現在與過去社會的一種連續,也代表著現在這個溷濁社會裡的一點希望、一些溫暖,至少不是所有人都是喪失人性的,還是有人堅持作自我,願意把他們良善的一面拿出來與人相處。這或許也是陳若曦的一種奢望吧—在這最艱難的時代裡,還是有人願意為這個社會點起一盞微弱的燭光,溫暖這個豺狼虎豹橫肆的冷血社會。 八、結語從美好的回憶裡對照今日生活的悽惶,陳若曦的慨嘆便不由而生;從早期大剌剌在小說裡一吐心中的不快、看法,到《尹縣長》時把所有大悲大喜的情緒藏起來,不再從文字上針鋒相對、張牙舞爪,而把那些個描述反諷、怨懟的想法拐了好幾個彎,放在一種極冷靜、極理性的天秤上去,讓讀者自己去發現事件的是與非。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中國大陸,陳若曦在寫作中,關心社會、人性的主題始終未變,然而從沸騰騰的一片愛土之心,到颼颼的情感冷卻、壓抑,陳若曦在情感的表達上如此劇烈的變化,是她沉寂了一段時間後,所作的反思、內省而蘊釀出來的嗎?或可未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陳若曦對於這片鄉土上的熱情,在經歷了文革後,驟減的程度是讀者們有目共睹、有跡可尋的—她在寫作心態上的轉折,從奔放到抑語—可以查覺的是她在對鄉土懷抱的真心赤誠,在共產黨掀起的十年文革中,是徹底的幻滅了。這樣夢想的幻滅促使她堅決的離開故土,踏上異域,在異域裡,陳若曦內心的掙扎、對於那片隔海而衍生的鄉愁,使她一思及便痛心疾首,無法不裝作漠不關心貌。這樣生命底層的艱熬使她不得不成長,而表現在她再度提筆的作品中,成長的是故事人物敘述的精細,成長的是情感表達的程度昇華,這種情感內斂的宣洩和深度,不但使讀者讀之更動容,或者可以說是陳若曦在國土和自身的生命旅程中,經歷了徹底失望的幻滅後,在思想和創作上粹鍊過的成長。
台灣作家陳若曦作品
| 陳若曦,原名陳秀美,台灣台北縣人,旅美作家。陳若曦的創作於七十年代以後進入黃金時期,其小說以寫實主義路線,並充滿現實政治色彩和感時憂民的情懷,著名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說集《尹縣長》,長篇小說《歸》等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