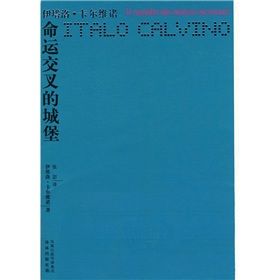編輯推薦
我的故事,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都包含在這些紙牌的交錯擺放之中,只是我無法將它從眾多的故事中分辨出來。我以一個不知其為何物的人的眼光觀察那些牌,根據一種圖像符號學進行解釋敘述,當偶然排列的紙牌,能夠讓我找到它們內涵的故事時我就動手寫出這故事。
內容簡介
《命運交叉的城堡》是一部由圖畫和文字組合的小說。卡爾維諾選擇塔羅紙牌,來構建小說的敘事結構。塔羅紙牌是十五世紀起風行義大利和歐洲的一種紙牌,可供四個人遊戲,也可用於占卜。在中世紀某個不確定的年代,在森林中的一座孤獨的城堡里,許多過往旅人前來投宿。這些旅人聚在一起,他們素不相識,都失去了說話的能力,塔羅紙牌成為他們之間進行交流的一種手段。他們按照每張紙牌上的圖畫,講述各自的冒險經歷。這些貴族、貴婦人、騎士、農民、工匠、馬夫,等等,講述了形形色色的故事,其中既有關於愛情、死亡、冒險、恐怖的故事,又有被出賣的國王、受傷害的少女等趣聞軼事。他們的命運遭際在這裡交叉、聯結,城堡便具有了一重象徵的意義:“命運交叉的城堡”。
《命運交叉的城堡》最先於一九六九年以豪華版刊印,僅在少數人中間傳閱,一九七三年改由埃依納烏迪出版社推出大眾版,得以廣泛流行,風靡一時。
作者簡介
卡爾維諾,關於生平,卡爾維諾寫道:“我仍然屬於和克羅齊一樣的人,認為一個作者,只有作品有價值。因此我不提供傳記資枓。我會告訴你你想知道的東西。但我從來不會告訴你真實。”1923年10月15日生於古巴,1985年9月19日在濱海別墅猝然離世,而與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
父母都是熱帶植物學家,“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學研究是受尊重的。我是敗類,是家裡唯一從事文學的人。”
少年時光里寫滿書本、漫畫、電影。他夢想成為戲劇家,高中畢業後卻進入大學農藝系,隨後從文學院畢業。
1947年出版第一部小說《通向蜘蛛巢的小徑》,從此致力於開發小說敘述藝術的無限可能。
曾隱居巴黎15年,與列維-施特勞斯、羅蘭·巴特、格諾等人交往密切。
1985年夏天準備哈佛講學時患病。主刀醫生表示自己未曾見過任何大腦構造像卡爾維諾的那般複雜精緻。
目錄
命運交叉的城堡城堡
受懲罰的負心人的故事
出賣靈魂的鍊金術士的故事
被罰入地獄的新娘的故事
盜墓賊的故事
因愛而發瘋的奧爾蘭多的故事
阿斯托爾福在月亮上的故事
其餘的所有故事
命運交叉的飯館
飯館
猶豫不決者的故事
復仇的森林的故事
倖存的騎士的故事
吸血鬼王國的故事
兩個尋覓又丟失的故事
我也試講我自己的故事
荒唐與毀壞的三個故事
前言
前言《命運交叉的城堡》於一九七三年十月由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出版。卡爾維諾在構成這本書的兩篇文字之後寫了一篇後記,詳細講述了這本書的構思和產生(以及出版)。在奧斯卡叢書的這個版本里,七三年的後記被用作了作者的前言。
構成本書的兩篇文字中,第一篇《命運交叉的城堡》於一九六九年首次發表在《貝爾加莫和紐約的子爵塔羅牌》上,出版者是帕爾馬的佛朗科·馬利亞·里奇。本版採用的與文字相配的圖畫就是為了喚起對里奇原版所印紙牌的色彩和尺寸的回憶。這是大約十五世紀中葉時波尼法喬·本波為米蘭公爵家繪製的一副牌,現在一部分收藏在貝爾加莫的卡拉拉學院里,另一部分則在紐約的摩根圖書館裡。本波所繪的一些牌已經流失,其中有兩張在我的故事裡非常重要,即魔鬼和高塔。因而我在書中提及它們時未能在書頁旁放置相應的畫面。
第二篇《命運交叉的飯館》是用同樣的方法,運用如今已經在國際上十分流行的塔羅牌(這種牌—特別是在超現實主義以後—在文學領域大為走運)構思的:B.-P.格里莫出版社的《馬賽的古老塔羅牌》(以一種被保羅·馬爾多訂正的“修訂版”方式)複製了一副於一七六一年由馬賽的紙牌製作師傅尼古拉·康維爾印製的塔羅牌。同原牌相比,這副牌在複製時雖然尺寸略有縮小,卻並沒有喪失原作的魅力,只是色彩稍遜一些。這副馬賽牌與今天仍在義大利的很多地方當作遊戲紙牌使用著的塔羅牌相比並無多少區別,只是義大利牌都是半身形象相對印成的,而這副牌的形象則是完整的,加之其粗糙和神秘的風格,特別適合於我根據各種可以作出不同解釋的形象而進行講述。
法國和義大利對占命牌的稱呼各有不同,法國人說的LaMaison-Dieu(教堂)被我們稱為LaTorre(高塔),法國人的LeJugement(審判)被我們稱為Angelo(天使),法國人的L誥moureux(情人)被我們稱為L誂more(愛情)或Gliamanti(愛人),單數的L誆toile(星)變成了複數的LeStelle(星辰)。我按照故事情節需要分別採用了最合適的名稱。(Lebateleur和IlBagatto在法、意兩種語言中都是來源不詳的名稱,其唯一肯定的意思就是,在兩種語言中它都是第一張占命牌。)
這種把塔羅牌當作組合敘事機器的構思,我是受到保羅·法布里的啟發,他在一九六八年七月烏比諾的一個關於敘述結構的國際研討會上做了《紙牌占卜術的敘事與紋章圖案的語言》的報告。在M.I.列科姆切娃和B.A.烏孜潘斯基的《作為符號系統的紙牌占卜術》和B.F.葉戈洛夫的《最簡單的符號系統與交叉的類型學》(其義大利文譯文見於由雷莫·法卡尼和翁貝爾托·埃科整理,一九六九年由米蘭的蓬皮亞尼出版的《符號體系和蘇聯的結構主義》一書)中,第一次對算命紙牌的敘事功能進行了分析。但是我不能說我的工作是利用了這些研究的方式。我從他們的研究中所獲取的主要是每張牌的意味取決於它在它前後的牌的行列中所占的位置這一觀念,從這一觀念出發,我獨立地按照自己文章的需要進行了工作。
至於解釋紙牌占卜術和塔羅牌象徵寓意的大量書目,儘管我早已閱讀知曉,但我相信它並沒有對我的工作產生多大影響。我以一個不知其為何物的人的眼光觀察那些牌,從中得出某些啟發和聯繫,根據一種圖像符號學進行解釋敘述。
我先從馬賽牌開始,試著把它們當作一張張分解圖按照故事情節順序排列組合。當偶然排列的紙牌能夠讓我找到它們內涵的故事時,我就動手寫出這故事;我逐漸積累了不少材料;可以說,《命運交叉的飯館》里的大部分故事就是這個階段里寫成的;但我一直不能把紙牌按照包容多重敘事的順序排列起來,只好不斷改變遊戲規則、總體結構和敘述方案。
出版商佛朗科·馬利亞·里奇邀請我為那本關於子爵塔羅牌的書寫一篇東西時,我正欲作罷。剛開始,我打算用已經寫成的那些故事,可是很快就意識到十五世紀微型彩畫的世界與馬賽牌大眾化印刷品的世界大不相同。不僅有些占命牌的圖像不同(力量是男人,馬車上是女人,星辰人物不是裸體而是著衣裝的),因此必須根本改變敘述的相關情節,而且圖像是以一個不同的社會背景為前提繪製的,因此另有其表現語言和情感。我自己拿來做參照的文學作品是《瘋狂的奧爾蘭多》,因為波尼法喬·本波的塔羅牌畫比路多維科·阿里奧斯托的詩要早差不多一個世紀,這些畫可以反映阿里奧斯托的想像所形成的那個可見世界。於是,我立即用子爵塔羅牌擺成按《瘋狂的奧爾蘭多》的方式啟發的故事線索;組成我的“魔法四方形”故事的交叉中心並不算難。只要能讓其他故事相互交叉起來,我就能創造出不是用字母,而是用紙牌形象組成的填格遊戲,而每一行無論橫豎都既能順讀又能反讀。我在一個星期之內就完成了《命運交叉的城堡》(而不是飯館),與該書其他內容一起印製成精裝本出版。
書一出版就得到一些志趣相投的批評家兼作家的認同,被一些研究者以科學的嚴謹在一些國際性的學術雜誌上進行分析,如馬里奧·科爾蒂(在海牙出版的一本雜誌《符號學》上)和熱拉爾·熱諾(在一九七二年八九月號的《批評》雜誌第303至304頁上),美國小說家約翰·巴思在他在布法羅大學的講座中談到了它。他們的態度鼓勵了我像我的其他作品一樣把它按照慣用方式發表,使之獨立於藝術書籍的彩色繪畫書刊。
但首先我想完成“飯館”,好讓它與“城堡”一起發表,因為大眾化的塔羅牌不僅可以印成黑白色的,而且很富有敘事魅力,而我在“城堡”里卻未能充分開發這種魅力。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也像排列子爵牌那樣,把馬賽牌組成交叉故事的“容器”。可這個工程我沒能成功:我想從我原先已經構思的一些故事出發,對那些牌我已經賦予了一定意義,故事也寫了很多,然而卻不能把它們擺進一個統一的框架結構里,我越是琢磨,每個故事就越變得複雜,就要牽扯上更多的牌,而那些牌已經用於其他故事,實在難捨難棄。我終日坐在那裡,把我的牌擺了拆、拆了擺,絞盡腦汁想出新的遊戲規則,勾劃出上百種框架,方陣、斜方形、星形,可總是把最重要的牌留在外邊,而不要緊的牌都能組合進去,框架變得非常複雜(有時變成三維立方體或多面體),搞得我自己都繞不清楚了。
為了走出這個死胡同,我丟開框架,重寫那些已經成型的故事,而不去考慮是否能在其他故事的網路里找到位置,可是我覺得只有依照一定的嚴格的規則所進行的遊戲才有意思,那就是每個故事都必須與另外的故事交叉,否則就分文不值。另外,當我開始動筆時,不是排列好的每行牌都能寫出好的故事,有些牌無法引發我的靈感,有些牌只能去掉才能保證文章的效果,有些牌卻能經得起反覆推敲,一下子就顯露出文字語言的連貫力量,一旦寫成就再無要更改之處。就這樣,我又按照新寫成的篇幅在重新組牌,需要考慮重建和拆除的工作量仍然在增加。
除了圖畫文字和寓言編寫工程上的困難,還有風格安排上的困難。我意識到,與“城堡”在一起,只有當兩部故事的語言再現出文藝復興時期的精緻微型彩繪與馬賽的粗糙塔羅牌在形象上的風格差異時,“飯館”才能具有意義。於是我儘量減少文字語言材料,直到它降到一種夢遊者的嘟嘟囔囔的水平。可當我試圖按這種編碼再寫時,那些作為文學參照的紙頁卻牴觸起來,阻止我寫作。
一次又一次,經過長短不同的間隔,我這幾年在這個迷宮裡捕獵,而迷宮很快就吞噬了我。難道我正在發瘋嗎?難道是這些神奇形象的有害影響不讓人不受懲罰就隨意擺弄它們?還是這種組合工程釋放出的龐大數目已令我頭暈目眩?我決定放棄,把一切都丟下,去忙別的事情:在一件我已經探索過其內涵但它只是作為理論假設才有意義的工程上,再花費時間,這是荒唐的。
又過了好幾個月,興許是整整一年,我再也沒有想它,可是在一個突然的瞬間我想到可以再用另外一種方法,更簡單、更迅速、肯定能成功的方法。於是,我又開始組織框架,修改,填充,又開始陷入活動沙堆之中,把自己套進怪癖頑念里不得自拔。有時我深更半夜醒來,跑去記下一個定型的修改方案,而它又引發沒完沒了的修改。還有的夜裡我帶著找到完美表達方式的寬慰心情躺下,可早上剛一起來就把這個方案撕碎。
現在終於問世的《命運交叉的飯館》就是這些艱苦創作的產物。作為“飯館”的總體方案的由七十八張紙牌組成的方陣沒有按照“城堡”組合的規則:“講述人”既不順著一條直線也不按照一定規程講述;有的牌在所有故事裡都重複出現,甚至在一個故事裡也不止一次出現。可以說寫成的文章是逐漸積累的材料的檔案館,經過對圖像解釋、性格情緒、觀念意向、風格體現分類而成的檔案館。我決定發表《命運交叉的飯館》純粹是為了解放自己。只要不出版,我還得手裡拿著書稿不斷修改、重寫。只有這本書印成發表,我才算終於能解脫出來,但願如此。
我還想說,有一段時間,在我的意向中,這本書應包括不止兩篇,而是三篇。我要找與這兩副牌相當不同的第三副塔羅牌嗎?到了一定時候,我對這種曠日持久的陷入逼迫自己按照一定思路進行創作的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圖像索引之中感到厭倦。我覺得需要尋求一種鮮明的對照,用現代視覺材料做類似的工程。但是什麼能充當現代塔羅牌代表這種集體的無意識呢?我想到連環畫,不是喜劇而是悲劇的、驚險嚇人的:歹徒,受驚的女人,宇宙飛船,迷人的女郎,空戰,發瘋的科學家。我想過跟“城堡”和“飯館”一起再寫一個《命運交叉的汽車旅店》:一些人在逃離一場神秘的災難後來到一家半毀壞的汽車旅店裡,那裡只有一份燒得剩下一張的報紙:連環畫版。倖存者們嚇得失去了言語能力,就指著畫面講述自己的故事,當然不按照原版的順序,而是從一格跳到另一格,或按豎線,或按斜線。我沒有按照我的思路繼續進行下去,就只停留在這點上了。我對這種實驗的理論和表述已經興趣索然,從任何角度看,都到了轉向其他事情的時候了。
一九七三年十月
精彩書摘
城堡在一片密林之中,有一座城堡向所有途中趕上過夜的人提供住所,不論是騎士還是貴婦,是王室的儀仗還是朝聖的平民。
我走過一座破舊的吊橋,在一進昏暗的院落中跳下馬,默不作聲的馬倌們接過了我的馬匹。我氣喘吁吁,兩條腿勉強撐住我的軀體:自從進入林中以來,我所經歷的種種考驗,奇遇、幽靈、決鬥,已令我無法讓自己的四肢和頭腦再聽指揮。
我踏上台階,走進一間高大寬敞的大廳:許多人——他們當然也是在我之前經由穿林的道路到達的過客——正圍著一張被一盞盞燭台照亮的餐桌用晚餐。
我環視四周,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或者應該說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感覺,在因為疲倦不安而稍有動盪的頭腦里混雜不清。我覺得像置身於一個富麗的宮殿中,這絕非人們所能指望在這如此偏僻鄉野的城堡里能遇到的:這不僅由於珍奇的陳設和精雕細作的餐具,而且也由於籠罩在所有用餐者中的那種寧靜和安逸:他們全都相貌堂堂,衣冠楚楚。與此同時,我還感到一種偶然,一種雜亂,甚至是一种放肆,仿佛這不是一個豪華優雅的家宅,倒是一個下等小旅館,一些身分和來歷各不相同的陌生人湊到一起過夜,不得不男女混雜,每個人都感到擺脫了在原來所屬的環境中應遵守的規矩,就像忍受不甚舒適的生活方式一樣,也在不同的更加自由的習俗中放縱自己。事實上,這相互對立的兩種印象都可以反映出一個主題:或許是,這個城堡因為多年來一直被視為過路驛站,漸漸退化成小旅館;而城堡的男女主人雖然總是保持著溫文爾雅的待客風度,也被人看得淪為店主一類的人;或許是,一個餐廳——就像人們常見的在城堡旁邊供士兵和馬夫飲食的酒店——只是因為城堡被遺棄多年,而擴展到原先豪華的大廳里,在那裡安放了長凳和木桶,而這些環境的堂皇富麗,加之顯要旅客的來來往往,為其增添了一種出人意料的尊嚴,使男女店主想入非非,最後竟認為自己就是一座宮殿的君主。
說真的,這些想法在我而言只是一瞬間的感受,更為強烈的,是發現我自己竟然有驚無險平平安安地置身於一些高貴者之中的那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