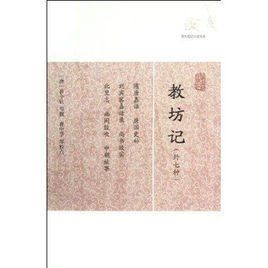基本內容
 教坊記
教坊記【本書簡介】《教坊記》系撰者為左金吾(掌東城戒備防務的主官)
倉曹參軍時,教坊中下屬官吏為其所述的教坊故實,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主要記述了開元年間教坊制度、有關軼事及樂曲的內容和起源。《教坊記》開始部分記述樂伎日常生活以及學藝和演出情況,中間列出325首曲名,包括《獻天花》、《和風柳》、《美唐風》等大曲46個,一般曲目278個,最後還說明若干樂曲和歌舞的來源,是研究盛唐音樂、詩歌的重要資料。宋代晃公武在《郡齋讀書志》中說開元中教坊特盛,令欽記之,率皆鄙俗,非有益於正樂也。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雖然有同感,卻又看到本書後記諄諄於聲色之亡國,意在示戒,其風旨有中取者,同時特別指出書中所列曲調名足為詞家考證。
【版本簡介】《教坊記》最早刻本為南宋《類說》本,曾慥編。另有《說郛》百卷本,元陶宗儀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儼山書院及青藜館原刻本;明嘉靖間(1522—1566)陸楫本;明天啟六年(1626)刻本;《古今逸史》收錄本明弘治間(1488一1505)郁文博補足百卷本;明末陶珽校訂一百二十卷抄本;明崇禎間(1628—1644);《續百川學海》本清順治三年(1646)重印121卷本;《唐人說薈》本,清陳蓮塘編,乾隆五十七年(1792)原刻本,清嘉慶、光緒間(1796—1908)重刻本,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清道光元年(1821)酉山堂復明刻本;民國四年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民國十六年(1927)上海涵芬樓據明本排印本;《古今說海》本;《五朝小說大觀》收錄本;《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收錄本;《香艷叢書》收錄本,清宣統三年(1911)上海圖書公司鉛印。今存較早善本為明鈔《說郛》本與《古今說海》本。
今有:《教坊記》文學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用宋刻補足明刻景印本;《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收錄本,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刊印;《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收錄本,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教坊記箋訂》,任半塘箋注,中華書局1962年版,亦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教坊記》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2000年版。
原文選載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歷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習。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中。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四門外,即苑之東也,其間有頃余水泊,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若其家猶在教坊,謂之內人家。敕有司給賜同十家,雖數十家,猶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曰十六曰,內人母得以女對,無母則姊妹若姑一人對,十家就本落余內人並坐內教坊對,內人生曰則許其母姑姊妹等來對,其對所如式。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居然易辨明。內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弦箜篌箏翟賄,謂ㄐ彈家。
開元十一年,初制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曰,便堪上場,惟ㄐ彈家彌月乃成。至戲曰,上令宜春院人為首尾,ㄐ彈家在行間,令學其舉手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擇釉賄為首尾。首既引隊,眾所屬目,故須能者,樂將闋,稍稍失隊,餘二十許人舞曲終,謂之合殺,尤要快健,所以更須能者也。
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制就縵衫。下才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繡窠也。舞人初出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即於眾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納懷中。觀者忽見眾女鹹文繡炳煥,莫不驚異。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戲曰,內會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不離此兩曲,余盡讓內人也。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鹿章}拂林大渭州達摩之屬,謂之健舞。
凡樓下兩院進雜婦女,上必召內人姊妹入內賜宴。因謂之曰:“今曰娘子不須唱歌,且饒姊妹並兩院婦女。於是納妓於兩院歌人更代上舞台唱歌。內妓歌,則黃幡綽讚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訾詬之,有肥大年長者即呼為屈突乾阿姑,貌稍胡者,即雲康太賓阿妹隨類名之,標弄百端,諸家散樂,呼天子為崖公。以歡喜為蜆斗,以每曰長在至尊左右為長入。
箸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又與長入趙解愁私通,侯氏有疾,因欲藥殺之。王輔國鄭銜山與解愁相知,又是侯鄉里,密謂薛忠王琰曰:“為我語侯大兄,晚間有人送粥,慎莫吃。”及期,果有贈粥者,侯遂不食。其夜裴大娘引解愁謀殺其夫,銜山願擎土袋,燈既滅。銜山乃以土袋置侯身上,不壓口鼻,其黨不之覺也。比明,侯氏不死,有司以聞,上令范安窮究其事,於是趙解愁等皆決一百。眾皆不知侯氏不淹口鼻而不死也,或言土袋綻裂故活,是以諸女戲相謂曰:“自今後縫壓婿土袋,當加意夾縫縫之,更無令開綻也。
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輩,有兒郎聘之者,輒被以婦人名號。即所聘者,兄見呼為新婦。弟見呼為嫂也。兒郎有任宮僚者,宮忝與內人對。同曰垂到內門,車馬相遇,或褰車簾呼阿嫂。若新婦者,同黨未達,殊為怪異,問被呼者,笑而不答。兒郎既聘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雲學突厥法,又雲我兄弟相憐愛,欲得嘗其婦也。主者知,亦不妒他,香火即不通。
蘇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慾得其速醉,多勸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契錘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為五奴,自蘇始。
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羝。(謂腋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