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當代小說家墨白創作的長篇小說“欲望”三部曲中的藍卷。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第1版(2012年4月1日)
平裝: 284頁
正文語種: 簡體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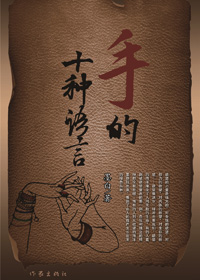 手的十種語言
手的十種語言開本: 16
ISBN: 9787506363099
條形碼: 9787506363099
品牌: 作家出版社
ASIN: B007UXD50W
“欲望”三部曲:
紅卷:《裸奔的年代》,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
黃卷:《欲望與恐懼》,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
藍卷:《手的十種語言》,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簡介
著名畫家黃秋雨失蹤兩天之後,屍體在潁河裡被一個漁人發現,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隊長方立言奉命偵破這起命案。他在調查中發現,黃秋雨生前創作的組畫《手的十種語言》中的最後十幅全部以女性裸體為內容,這其中牽涉到了市委書記的妻子,而黃秋雨被盜的日記和繪畫,似乎都與這有關。就在命案調查接近真相的時候,被追捕的犯罪嫌疑人突然死於一場車禍,而兩年前試圖謀殺黃秋雨的兇手也浮出水面,使案件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關 鍵 字: 黃秋雨 女性裸體 市委書記 手指 小說 兇案
作者簡介
墨白
作家,河南淮陽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夢遊症患者》、《映在鏡子裡的時光》等;中篇文集《航行與夢想》、《尖叫的碎片》、《局部麻醉》、《瞬間真實》、《幽玄之門》、《雨中的墓園》六卷;小說集《孤獨者》、《愛情的面孔》、《重訪錦城》《事實真相》、《霍亂》、《懷念擁有陽光的日子》、《神秘電話》、《六十年間》等。作品還被翻譯成英文、俄文、日文等多種文字。
其它作品:
欲望與恐懼
來訪的陌生人
目錄
01:死者
02:被盜的畫室
03:手的十種語言
04:黃秋雨的手稿
05:米慧寫給黃秋雨的信
06:米慧寫給父母的信
07:在凌晨玩偷菜遊戲的禿頂男人
08:蓄謀的跡象
09:現場
10:兩年前的懸案
11;對金婉的調查
12:米慧的詩
13:米慧寫給黃秋雨的信(續)
14:對作家譚漁的調查
15:黃秋雨的詩作及其評論
16:關於黃秋雨社會活動的資料
17:對《手的十種語言》的構想
18:《手的十種語言》中關於歷史的部分
19:案情分析
20:粟楠寫給黃秋雨的信
21:黃秋雨隨手寫在書籍上的文字
22:25張匯款收據
23:米村——潁河鎮
24:譚漁回憶黃秋雨的文章
25:在陰冷的畫室里
26:謀殺者
27:欲望之手
“欲望”三部曲後記
在連綿不斷的秋雨里,我最終完成了“欲望三部曲”的寫作。
《欲望》中的紅卷寫於1992年11月至1999年5月之間,黃卷寫於2000年前後,而等完成最後的藍卷,時間已經到了2011年的秋季。在這十九年間,因為《欲望》的寫作,我走過太多的地方,斷斷續續,長路漫漫,終於,在今天,將結束於這寂靜的山林。
我說的是寂靜,而不是寂寞。儘管,山上避暑的人早在八月底都已經下山,現在已經到了九月的中旬。每天早餐後,我就在別墅的窗前面對森林坐下來,開始寫作。從2011年的6月開始,一直到9月中旬,我都在做著結束這漫長的寫作的工作。從《裸奔的年代》到《欲望與恐懼》,從《欲望與恐懼》到《別人的房間》,《欲望》確實耗去了我人生太多的心血。
《欲望》里所講述的故事是從二十世紀最後兩個年代開始,直到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年代的中期結束,時間跨度三十年,在精神的承接上、在物理時間與歷史背景上都構成了延續的關係。《欲望》里所呈現的這個時期,“蛻變”這個詞最能體現我們這個民族精神上的進程。在剛剛過去的世紀更替的年代裡,由無數人離鄉背井所構成的巨大運動,就是對“蛻變”這個詞的最好註解。在我們身邊,在中國版圖上大大小小的城市,每一片可以生存的空間都漂泊著來自異鄉的身影和陌生的聲音,我們能從他們身上折射出來的嚮往和夢想、幸福和痛苦、希望和無奈、歡樂和尷尬、情愛和仇恨里感受到,這一切,都和我們的形與質的改變有著密切的關聯。“蛻變”的過程是痛苦波折的,“蛻變”的結果是矚目驚心的,而我們精神上發生的所有“蛻變”的動力,都源自欲望。
欲望的力量是強大的。對金錢的欲望,對權力的欲望,對肉體的欲望,對生存的欲望,欲望像洪水一樣衝擊著我們,欲望的海洋淹沒了人間無數的生命,有的人直到被欲望窒息的那一刻,自我和獨立的精神都沒有覺醒;而有的人則從“欲望”的海洋里掙脫出來,看到了由人的尊嚴生長出來的綠色叢林。我稱這種因欲望而產生的蛻變為精神重建,或者叫著精神成長。西班牙哲學家和小說家喬治·桑塔雅那(1863—1952)曾經告誡我們:“即使全世界都獲解放,但一個人的靈魂不得自由,又有何益?”一個連尊嚴都沒有的人,何談靈魂的自由?應該說,人的尊嚴是我寫作《欲望》時思考最多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伴隨著我走過了漫漫長夜,等到了2011年炎熱的夏季,我下決心結束我這夢境一樣的旅程。可轉眼,天氣已經變得陰冷起來,似乎連日的陰雨都擁擠到我現在所居住的空間裡。
無風霧起的時辰,我像待在不見天日的海底世界。除去風,除去落葉,除去鳥鳴,整個寂寥的空間裡,出出進進只有我一個人。除去農曆單日的早晨,我早起去南街趕一次山裡的露水集,從山民手上買來維持生命的食物外,其餘的時間就是創作。日子清苦而寂靜。我說的是寂靜,而不是寂寞。我不寂寞,那是因為我常常想起我舊日的朋友,譚漁、吳西玉;我不寂寞,因為我每天所要面對的都是一些我熟悉的人物:米慧、金婉、林桂舒、粟楠、方立言……當然,還有黃秋雨,一個我所熟悉的畫家。
當我面對黃秋雨留下的文字時,我就像看到了一個精神病患者,一個神秘幻想者,一個精神流浪者,一個現實生活的夢遊者,一個癌症病患者,而更多的時候,他是一個有著痛苦的靈魂、有著非凡創造力的藝術家。我從他泥沙俱下的文字里,在他尋找失去的愛情的路途中,我深刻地體會到了他對生命的熱愛與無奈,他孤獨的內心世界和庸俗的社會現實構成了巨大的衝突。我清楚地看到,一個人內心的巨大的痛苦,是怎樣被我們這些麻木的靈魂所忽視,世界到了黃秋雨這裡,徹底呈現出了無限的冷漠。而我,卻是用了這冷漠,來充實我這孤獨的寫作生活。其實,在這漫長而孤獨的創造里,我的內心有著無處不在的寂寞和孤獨,只是我不願意承認而已。我之所以不願意承認這寂寞和孤獨,更多的時候是因為我的朋友譚漁、吳西玉和黃秋雨,這同一天出生的三兄弟,痛苦與壓抑、焦慮與迷茫、欲望與恐懼、掙扎與絕望等等這些滲透了他們的精神世界。他們各自不同的生命體驗和個體存在構成了一幅複雜的精神圖像。
在無人走過我房前那長長的石台階的時候,我就把我的朋友方立言拉出來坐在廊台上,面對遠處的山崗一起閱讀在《別人的房間》里出現的文獻,那些寫在不同書籍上的隱藏在書櫃裡的文字,那些女孩寫給黃秋雨的書信,那些新聞資料,那些歷史故事,那些回憶錄,那些繪畫,那些充滿情慾的詩歌,那些充滿理性的詩歌評論,甚至是一張很久以前的匯款收據……在我們一起閱讀那些關於黃秋雨的文獻時,一些潛在的意識在閱讀的時候會突然冒出來,我們會因思考而停頓,我們會因某些可疑的事件發出自己的聲音。在這個過程中,兩個不同的“我”會在同一行文字里出現,這種雙重的第一個人稱和視角,真是一次奇妙的敘事實踐。“個人的自我是理解美學價值的惟一方法和全部標準”(哈羅德·布魯姆語),我心理清楚,整部《欲望》都是一次純美學的追求,我已經完全拋開了譚漁、吳西玉和黃秋雨他們所處的社會背景,迷失在了具體的文本語境之中。這就是我堅持我只有寂靜而沒有寂寞的原因,我覺得,我的生命完全和出現在我小說里的人物融為了一體,我成了他們蓄謀的一部分。
連綿的陰雨使時光仿佛蹣跚地行走到了深秋。從山坡下通向我門前的長長的石台階上,再也看不到一個遊人。晚飯後,我撇下我的朋友在別墅里,獨自打著雨傘去散步。我所居住的十八棟別墅後面的那些山路上,確實顯現出淒涼來,滿眼被秋雨打濕的黃葉緊貼在石壁上,那些隱藏在樹林里的別墅古老的門上,是前些日子被年輕的女護士離開時貼上去的蓋著紅色印章的封條。在那些要等到明年才能開啟的房門後面,已經是深不可測的灰暗,就像躺在手術台上等待被人解剖的黃秋雨,他已經關閉了自己的房門,讓我們再也無法走進他那複雜而神秘的房間。是的,誰也無法啟開那幢世界上獨一無二建築的房門,我們只能通過他身邊那些貌似熟悉他的人的口述,或者一些與他相關的文字來了解他。其實,我們所有過世和在世的人,都是另外一個黃秋雨,都是另外一個吳西玉、都是另外一個譚漁。有些時候,我們就是那些被貼了封條無法進入的房間。不可理解的是,我們這些人,我們這些平庸的人,面對身邊一個深處痛苦的生靈,往往是視而不見。可是,當他離開人世後我們卻又總是想違規撕下那房門的封條,企圖進入房間的內部,去窺視尋找他們的隱私,以供我們酒前茶後取樂的談資。這就是我們所處的世界。
《欲望》里的文字,都以長篇小說或者中篇小說的形式分別刊登在《收穫》、《花城》、《十月》、《芙蓉》、《江南》等不同年份的文學期刊上,現在,她們終於以一部完整的長篇小出版。在寫作《欲望》斷斷續續的時光里,正是我人生的路途中最為茫然的時期,痛苦憂鬱和孤獨,都是我對生命最為真切的體驗。是的,在秋雨飄搖的山路上,我再也看不到一個人影,但是卻能聽到幽靈在山間低語。所有的靜默,都歸還給了那些隱藏在樹林間的一幢接一幢古老的別墅,那些由西方人在一百多年前留下的,現在被年輕的女護士貼上封條的別墅。當然,幽靈的低語仍然沒有終止,那幽靈附身於秋雨里時而飄落的黃葉,或者那些躲藏在別墅廊台上鳴叫的不知其名的鳥類。
作者:
2011年9月13日,雞公山,廣東軍區療養院,北崗18棟
關於《手和十種語言》的評論
復調的發生與轉換——閱讀墨白的《手的十種語言》
張延文
1929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48年後,巴赫金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問題》,對於陀氏進行了重新解讀。在該書中,巴赫金指出陀氏小說的高明之處在於具備了復調特質。在巴赫金看來,陀氏的小說當中的主人公都有其相對獨立的意識,主人公與作者之間形成了平等的對話關係。⑴復調體現出的是人與人之間的自由、平等和交流關係;與復調相對的是獨白,獨白則意味著壓制、等級和隔離。
巴赫金的復調理論一經推出,就在文學藝術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幾十年來一直備受推崇。復調理論從最初的小說理論,逐步演繹推廣到整個文化詩學領域。復調理論雖然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引入到中國,但對其的關注度也是很高的。比較遺憾的是,這方面的研究雖然在國內已經相當充分,卻因為缺乏具備了復調性質的小說文本而無法真正得到充分的闡述和實際套用。這一方面是因為缺乏具體的社會語境,另外一方面也和文學創作的水平尚未達到世界水準有關係。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加速,部分地區已經出現了後現代社會的文化特徵,信息文化的影響日益廣泛深入;同時,國內文學界的創作也出現了深化的趨勢,一些代表性的作家,比如墨白,其部分小說文本具備了復調的特徵。而墨白近期出版的《手的十種語言》的復調特性尤為明顯,這部長篇小說的推出,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完美的中國版的復調小說的文本。這本書所擁有的文化詩學方面的象徵意義相當深遠,不僅代表了中國當代小說創作已經達到了世界一流的藝術水準,而且標誌著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也進入到了一個全新的時期。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國內小說界出現了先鋒小說創作的熱潮,其中包括馬原、格非、洪峰、莫言、殘雪等作家創作出一大批先鋒派小說,在語言、敘事等方面進行了大膽的嘗試,但由於缺乏相應的社會語境作為創作的底色,這股潮流很快就退卻了。而自九十年代開始在文壇嶄露頭角的新生代小說家則逐步顯示出其蓬勃的創作活力。作為新生代作家的代表性人物的墨白在九十年代初就是以其作品的先鋒性而受到文壇的關注。多年來,墨白在小說敘事方面做出的努力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他對於“欲望三部曲”的寫作就是最好的證明。墨白的“欲望三部曲”是其宏大的“潁河鎮”文學藝術王國版圖的重要構成部分,三部曲分別以同一天出生於潁河鎮的三兄弟譚漁、吳西玉和黃秋雨為主人公,描述了他們各自通過艱辛努力從鄉村走向城市,從幼小走向成熟、衰老甚至死亡的生命歷程。“三部曲”既互相關聯,又各自獨立,不僅表現了豐富多元的主題,在小說敘事上也呈現出了迥異的格局,而作為最後一部的《手的十種語言》的藝術創新尤為突出。
《手的十種語言》圍繞著一宗命案展開的敘事,刑偵支隊長方立言在著名畫家、錦城師範學院藝術系主任黃秋雨之死案進行偵察的過程當中的所見、所聞、所感構成了書的主體部分。該書使用的是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書中的“我”即方立言。這樣,書中的第一主人公黃秋雨就轉入了幕後,而“我”——方立言走向了台前,書中所有的人物、事件都必須經由“我”的行為的“召喚”才能進入到故事的進程當中。這類似於海德格爾在《面向思的事情》⑵當中提及的所有在場的事物必須經由“此在”才能顯示其自身的哲學命題。在海德格爾看來,人類歷史就是存在的真理被遺忘的歷史;使得事物成為事物的存在就是“無”,“無”需要敞開、澄明,才能通過去蔽化的過程來展示自我。墨白通過近似於存在主義式的哲學轉換,使得所有日常存在的事物基於“我”之思來接近於澄明之境,實現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也使得《手的十種語言》通過文本有意味的結構轉換而使其接近了哲學的奧義。
在書的“後記”里,作者饒有意趣地談起由於敘事所引發的奇妙經驗:“那些寫在不同書籍上的隱藏在書櫃裡的文字,那些女孩寫給黃秋雨的書信,那些新聞資料,那些歷史故事,那些回憶錄,那些繪畫,那些充滿情慾的詩歌,那些充滿理性的詩歌評論,甚至是一張很久以前的匯款收據……在我們一起閱讀那些關於黃秋雨的文獻時,一些潛在的意識在閱讀的時候會突然冒出來,我們會因思考而停頓,我們會因某些可疑的事件發出自己的聲音。在這個過程中,兩個不同的‘我’會在同一行文字里出現,這種雙重的第一個人稱和視角,真是一次奇妙的敘事實踐。”⑶《手的十種語言》採用了非常複雜而玄妙的敘事結構,不僅僅讓閱讀者獲得多重的心理體驗,即使是作者本人,也會在敘事的過程當中感受到它的迷人之處。在文本當中,“我”承擔了敘述者的功能,而“我”卻僅僅是作為故事當中的一個人物出現,這個人物在一開始僅僅是“黃秋雨死亡事件”的旁觀者,“我”以窺視的視角全面介入到與黃秋雨有關的所有人和事物,並對其加以“客觀”的評判,試圖探尋黃秋雨人生的非常之處。當然,隨著案件偵破的一步步推進,“我”也逐漸深陷事居,那種“局外人”的角色感逐漸消失,融入到了龐大的當下語境當中。
顯然,文本中的“我”和真正的敘事人是兩種存在,“我”只是故事裡的一個人物,敘事人則是作者,而作者還具備了“隱含的作者”和真實的作者兩種身份差異,只有在文本的敘事當中呈現了自我的那個作者才對文本起到了作用,也就是“隱含作者”;而獲得了敘事後的情感體驗的,則是作者本身。在接受過程當中,讀者無法真正了解作者的意圖,只能通過文本當中體現出來的審美趨向去推測隱含作者的意圖所在。作者與“隱含作者”之間的敘事情態的差異,是保證文本多元化主題的關鍵所在,正是由於墨白在進行敘事時所帶有的明顯的中立態度,儘量讓文本當中的人物去獲得自我表達的機會,才使得墨白感嘆那種擁有“雙重的第一人稱和視角”的神奇之處。承擔著第一人稱敘事功能的“我”,即方立言,作為一個刑偵人員,對於事件儘量採取客觀、公正的立場,並且從始至終保持著強烈的對於事實真相的探求欲望。這也讓文本當中的兩個“我”,即隱含作者和方立言都擁有了一個相對客觀的立場,這是小說具備復調特性的首要保證。
在《手的十種語言》當中,還有著大量的圍繞著黃秋雨存在的文獻資料,必須強調的是,毫無疑問,黃秋雨在書中是最為重要的角色,但他的角色功能也僅僅局限於他自身。敘事者顯然並沒有因為黃秋雨這個第一主人公而取消其他人物的獨立性,而方立言作為一個調查人員,更不會因此改變個人的情感態度。事實上,黃秋雨從一出場就已經死亡,他喪失了直接訴說的功能,只能通過各種文獻資料來進行間接敘述。這些文獻資料包括他與兩個情人米慧和栗楠之間的信件,有關黃秋雨的新聞報導,黃秋雨的繪畫、詩歌,黃秋雨的藏書,以及各類的歷史故事等當中直接、間接地表達出來。而這些已經逝去的事物,在生者的召喚下,一一恢復它們真實的面目,重新獲得了生命力。即使是還活著的黃秋雨的情人林桂舒,也是通過黃秋雨在書上寫的文字以及她寫的通訊稿和做的錄音來間接出場的。只有黃秋雨的妻子金婉,作為黃秋雨的四個女人當中的唯一一個明媒正娶的老婆,獲得了直接出場來表達自我的機會。這種安排或許也有著隱喻的成分,那就是說,金婉是在黃秋雨事件當中,是唯一的有合法的話語權的女人,而其他三個女性,則只是一種隱秘的存在,是黃秋雨私生活當中不合法性的存在,也是其最終死亡的真正誘因。金婉對於黃秋雨的表述和評價,帶有強烈的個人情感,和其他三個與黃秋雨相關聯的女性對於黃秋雨的評價有著巨大的反差,她一再強調黃秋雨的無能和無德。在這裡,讓我們聯想到日本電影大師黑澤明導演的經典影片《羅生門》,它們之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每個人眼裡的世界是迥然不同的。只有在強大的外在力量的壓制和強迫下,事物才會呈現出一致性的假象。
當我們翻閱書中大量的信件,會發現在這些信件當中存活著的鮮明的人物情感。比如通過米慧寫給黃秋雨的信件和情詩就塑造出了一個敢愛敢恨、有血有肉的才女形象,她對於黃秋雨的情感既有敬慕和熱愛,也有嫉妒和熱烈的肉慾。在這裡,米慧是靠著她自身的情感邏輯來獲得她自身的生命意義的,她有著個人的欲望和要求,她憑著自己的信件和詩歌來證明她自身的存在價值。在已經失去的時光里,留存著個人的思想和情緒。對於米慧的詩,譚漁和方立言都有著自己的看法,譚漁對米慧的詩讚不絕口,而方立言卻大謬不然:“丁聲樹離開後,我希望譚漁能就米慧的詩說下去。說實話,上面這些詩酸酸的,我還真沒有看出好在哪裡。無外乎就是談情說愛,要死要活的”。⑷書中這個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描寫,卻為其復調的藝術特質的完美的詮釋,書中人物的思想情感以及發展的歷程都真實可靠,且從不互相替代和兼容,顯得自由、豐富與多元。
《手的十種語言》當中大量存在的各類文獻資料,提供了小說文體之外的各類文體體裁,如新聞報導、信件、詩歌、檔案等等,另外還有繪畫等藝術形式,使得文本有著拼貼的特點。“拼貼”作為一種藝術表達手段,是從結構主義向後結構主義(也稱解構主義)轉向的重要特徵之一,是後現代主義的典型特點。拼貼本身就有著各類事物在一種不要求整體一致性的基礎上獲得平等相處機會的可能性,也就是一種更為廣泛意義上的復調,基於文化詩學價值上的復調。因此,在這種意義上來說,《手的十種語言》已經超越了單純基於文學藝術角度的復調性,而具備了基於人類社會文化價值上的復調,從而擁有了更為深入、廣泛的詩學內涵。這也同時賦予了小說文本以後現代主義的多元性價值。比如文本當中關於手的六幅圖畫,每幅圖畫下面配有註解,這有效拓展了文字難以表達的抽象內涵,打破了文本單一敘述的局限性。
小說文本里的物理時間只有短短的兩天,而其主人公黃秋雨涉及到的心理時間則長達三十多年,基本上包括了新時期以來所有重要的社會時期,也就是黃秋雨從農村進入城市生活所經歷的個人生命史的完整展現。而當我們閱讀完小說後,會發現文本當中展示的時間跨度遠遠不止三十幾年,比如書中關於十種“手的語言”而寫成的歷史故事,它們涉及到的故事時間可以推及文化大革命、大躍進、反右甚至新中國成立之前的解放戰爭時期。這些故事都可以獨立成篇,具有著完整的故事時間和空間。當中涉及到遇羅克、傅雷、沙飛、弘一法師等真實人物的歷史事件,它們所具備的時空價值帶有強烈的象徵意義,將真實的巨大的歷史事件植入小說文本當中,從而為“虛假”的敘述帶來了廣闊、真實的歷史場景,彌合了小說敘述和歷史事件之間的裂縫。這樣多重存在的立體時空組合,也是小說復調特性的具體體現。在講述到傅雷和夫人雙雙自殺這個事件時,有如此義憤填膺的追問:“所有的這一切都讓我想不明白,為什麼死呢?沒有怨恨的離別。你們說,是什麼束縛了他們的手,那雙把被單撕成條條的手,那雙把布條結成繩子的手,那雙把自己的脖頸送到繩套里的手。”⑸是什麼使得一個人會去心甘情願地將自己寶貴的生命親手毀滅?個人的生命價值在面對一個巨大的外在時,到底有多大的可抵抗性?當個人的生命尊嚴不能得到維護時,其生存的價值還有多大?這一系列的追問都在為黃秋雨之死鋪墊著社會語境,同時也使得我們深深反省文本展現的黃秋雨個人死亡背後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
當然,在《手的十種語言》當中大量出現的還有東西方的更為廣闊的文化背景,比如黃秋雨在國外留學的經歷,以及他畫作里出現的西方大師的影子,而夾著栗楠寫給他的信的書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黃秋雨寫給桂舒的信則在《印度壁畫》一書里,黃秋雨贈給錦城博物館的畫作則分別為《老子歸隱圖》和《伏羲創世圖》。這些都為黃秋雨思想行為來源做出了巧妙的腳註,同時也使得故事的主題上升到了全部人類文化史的主題高度。如果說,墨白的新作《手的十種語言》在文本的具體敘述上為我們呈現出了一部典型的復調小說的樣本的話,它所具備的當代的文學史價值就在於為中國當代文學提供了優秀的復調小說,填補了相關領域的空白;而其文化詩學的價值則在於以文學的樣式試圖突破文學的局限,使得個體生命的尊嚴和價值在一個宏大的社會意識形態當中得到彰顯,並使得基於個人生命經驗的個體生命史能夠突破根植於古老的文化傳統當中的集體歷史敘事的重重封鎖和壓制。這也恰恰是復調藝術所希望達到的終極價值。從一個更為巨觀的背景來看,墨白的《手的十種語言》可能還有著更為深刻的穿透力,它將所有事物在獲得了自身的特定的時空域的前提下,得到了一個眾聲喧譁的無物之境。這也意味著復調的統一也許恰恰在於“有生於無”、“有即是無”、“色即是空”等古老然而常青的哲學主題。我們從中看到的也許是在幻變無常的魔法時代,人性在澄明之境即將出現之前衍化出的光怪陸離。
注釋:
⑴(俄羅斯)巴赫金著,劉虎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6月版。
⑵(德)海德格爾著,陳小文、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3月版。
⑶墨白著,《手的十種語言﹒後記》,第274頁,作家出版社,2012年4月版。
⑷墨白著,《手的十種語言》,第105 頁,作家出版社,2012年4月版。
⑸墨白著,《手的十種語言》,第145 頁,作家出版社,2012年4月版。
——讀墨白的長篇新作《手的十種語言》
劉宏志
墨白是一個有著強烈文體意識的作家,他近年來的小說幾乎每一部都致力於文體上的創新與拓展。他的長篇新作《手的十種語言》(作家出版社,2012年3月版)以刑偵隊長方立言對著名畫家黃秋雨死亡案件的調查來展開敘事,但內容卻由大量的書信、書面文字、詩歌、詩評、新聞報導、歷史事件、回憶錄、調查手記、繪畫等多種載體和不同當事人的陳述所構成,顯然,墨白再次把文體的創新和內容的表達有機地結合了起來。
在長篇小說中嵌入日記、詩歌、散文等雜語並不罕見,或者說是一種常態。巴赫金就明確指出,“長篇小說是用藝術方法組織起來的社會性的雜語現象,偶爾還是多語種現象,又是個人獨特的多聲現象。”所以,長篇小說中嵌入各種雜語用來從側面印證,或者豐富小說表達的主旨也成為眾多作家自覺的選擇。但是,在墨白這部小說中,種種的文獻資料不是僅僅用來表達、印證作家表達的主題的,而它們本身就是小說的主體,是小說所要表達的主題本身,方立言的探案過程就是把所有與黃秋雨有關的各種文獻資料喚醒復活的過程。在小說里,黃秋雨的書信、手稿,以及米慧、粟楠寫給黃秋雨的書信,從邏輯上並沒有統一的完整性與嚴謹性,換言之,這部小說,就是用與黃秋雨命案有關的許多碎片來結構的,這些碎片就是小說的主題。這些沒有邏輯性、整體性的碎片並不是死板的組合,而是被方立言情緒化的閱讀而激活,那些本來就十分生動而感人碎片在我們的視野里生長起來。比如我們從米慧和黃秋雨的信就能看到一個絕望的、痴情的女子的情感掙扎,看到一個中年男子的情感的痛苦糾結。但是,這些感人的碎片卻不給我們的閱讀提供完整的、系統的結論。我們從這些碎片裡感知到了黃秋雨情感世界的豐富和痛苦,但是,我們所見到的這些豐富和痛苦卻不過是他情感世界的一斑而已,只到小說最後,我們也不能對黃秋雨這個人做出一個系統完整的評價,從而自然呈現出這部小說——在我看來——要闡明的具有哲學意味的主題:關於人的不可認知性。當我們認識到這個常常被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所忽視的主題時,那些小說中的碎片就變得閃閃發光,從而產生出具有深廣的文本價值。小說在通過碎片的拼接為我們打開了關於黃秋雨認知的多種可能性,由此勾勒出黃秋雨的一生,但同時,也宣告了這種勾勒的無力——我們無法對黃秋雨生命中深邃的精神世界做出一個系統的評價——這就是我們生活在現實中每一個人尷尬的處境。
在社會現有的話語系統中,我們習慣於對一個人做出簡單直接的價值評判,雖然這些價值評判都是以我們的某些印象碎片為基礎總結出來的,但是,這些評判一旦上升到蓋棺論定的層面,似乎就具有了某種不容置疑的權威感,好像我們真的能夠對一個人做出全面、透徹的認知。《手的十種語言》通過眾聲喧譁,互相纏繞又互相互拆解的關於黃秋雨的言論、信件,給我們展示了認知一個人是有多么的困難。從這個角度看,我們顯然應該對我們過去簡單粗暴的認知感到羞愧。顯然,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其他人都是一個神秘的存在,我們都無法對這個人做出全面系統的評價。從這個意義上,墨白這部小說所採用的形式就具有了獨特的象徵意義。藉助對別人的印象是我們認知其他人的重要方式,而且我們也已經習慣認定這種認知是沒有問題的,是可以觸及到被認知對象的根本的。可是,《手的十種語言》告訴我們,我們對很多事情、很多人的認識,其實都只是自以為是的一些碎片,而沒有觸及到這個人真正的內心世界。
墨白在這部小說中對黃秋雨的塑造,從文本上就已經具有了突破僵硬話語對人思想的禁錮的力量。當小說完全以各種話語碎片結構在一起的時候,當我們無法在這些話語碎片背後找到某種固定的僵化的邏輯理路的時候,這些話語碎片就具有了獨立的生命,每一個碎片都在向我們昭示著黃秋雨生活的某種可能性,但是,又沒有把這種可能性限定為唯一確定性。換言之,這種碎片式的拼接使得小說充滿了縫隙,充滿了闡釋的空間,能夠帶給讀者無數的聯想,給讀者留下了無窮的想像空間,這就使我們無法武斷地給黃秋雨的生命下一個定論。小說對主人公黃秋雨的獨特的塑造方式,給我們展示了作家對人類認知的思考,在這個世界上,我們除了真正知道自己,對其他任何人,我們所知道的,都不過是一些印象的碎片而已。小說中這些互相纏繞又互相拆解的相對獨立的資料碎片,以不加修飾的方式組合在一起,構建起作品的整體內容,使得其具有了更大的開放性,使作品形式本身獲得了獨特的意義。
——評墨白長篇小說《手的十種語言》
王春林
《手的十種語言》是墨白新近創作的一部具有強烈實驗色彩的先鋒小說。如同既往,這部小說的故事依然與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墨白小說標籤的潁河鎮存在著密切關係。熟悉墨白小說的讀者都知道,他的小說故事差不多全部發生在潁河鎮。只不過這一次,墨白所借用的是一種偵探小說的外殼。敘述者“我”名為方立言,是錦城市公安局刑偵支隊的支隊長,小說開始的時候,他正在負責勘察偵破一件殺人焚屍案。就在此時,一樁新的命案發生,死者是在當地很有名氣的畫家黃秋雨,由於他不但是錦城教育界、藝術界的名人,而且是市政協委員,身份地位非同一般,所以,局裡立刻決定,把方立言抽調回來負責黃秋雨命案的偵破工作。就這樣,對於這一命案的調查偵破就成為了小說敘事展開的過程。然而,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關注的是,對於墨白來說,他並不想把自己的小說變成真正意義上的一部偵探小說,因為到了小說結尾處,我們不僅沒有看到案件的真相大白,讀者反而如墮五里霧中,越發顯得撲朔迷離莫衷一是了。不容忽視的是,按照方立言他們的調查結果,黃秋雨的命案似乎與身為錦城市委書記的陸浦岩之間,存在著難以被忽略的密切關係。如果換了另外一個對於中國社會現實問題有著強烈興趣的作家,肯定會沿著這樣的一條敘事脈絡,把作品演繹為一部具有社會批判色彩的官場小說或者社會問題小說。由一樁命案的偵破而引發出重大的社會問題,本就是我們許多作家一種自覺或者不自覺的藝術思維方式。但墨白卻並不屬於這樣一種對於小說的社會學意義保持濃烈興趣的作家。對於墨白而言,以小說的形式對於人性世界或者說對於現代人複雜深邃的精神世界進行深入探究,很顯然是更有吸引力的一件事情。
在偵破黃秋雨命案的過程中,一些與黃秋雨關係密切的人物漸次地浮出水面。首先是黃秋雨的兩位學生情人。一個名叫米慧,另一個是粟楠。畢業於大學中文系的米慧,不僅溫柔多情,而且還極有文學才華。作為與黃秋雨年齡相差多達25歲的情人,她內心裡狂熱地愛著黃秋雨。這一點,自有她寫給黃秋雨的那些情書與情詩為證。粟楠的出現,要早於米慧。從她寫給黃秋雨的信件判斷,粟楠同樣非常狂熱地愛著黃秋雨。兩位情人的共同遭遇,一是都曾經為黃秋雨懷過孩子,二是都曾經試圖與黃秋雨結合而不得。但是,相比較而言,粟楠的命運要比米慧悽慘許多。粟楠不僅最後被送進了精神病院,而且,根據黃秋雨的好朋友作家譚漁的說法,粟楠在自己所懷的孩子流產的那一年,因為遭遇車禍而變成了植物人。而這,也正是黃秋雨之所以長期給粟楠匯款的根本原因所在。然後,是黃秋雨的另一位情人林桂舒。按照黃秋雨留在自己若干本圖書字裡行間的傾訴文字來看,黃秋雨對於這位現任市委書記的夫人有著極深的感情。從故事情節發展過程中流露出的一些蛛絲馬跡判斷,或許正是因為市委書記早就察覺到了這一情感的存在,所以才會有這次黃秋雨命案的形成。在這裡,我們必須注意到小說中的這樣一種暗示性描寫:“夜裡,我失眠了。一個又一個與黃秋雨命案有關的線索從我的腦海里閃過,胡中德?胡中德……難道,這兩個案子有著相同的因素?陸浦岩?不能確定,要有證據,證據!”這裡提到的胡中德,正是小說一開頭另一樁命案的殺人者。因為懷疑被殺者強姦了自己的妻子,所以胡中德才最終殺人焚屍的。此處方立言所謂“兩個案子有著相同因素”的懷疑,所強烈暗示出的正是陸浦岩存在著謀殺的可能。
這樣,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自然也就浮現在我們心頭。那就是,黃秋雨為什麼會前後有好多位情人呢?難道說黃秋雨是一個現代的唐璜,現代的花花公子么?黃秋雨的天生多情,一方面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也只有在接觸了他的妻子金婉之後,我們才能夠理解黃秋雨為什麼會執意在自己的婚姻之外尋找來自於異性的感情慰藉。儘管只是與方立言之間並不太長的一席對話,但市民女子金婉的俗不可耐就已經躍然紙上了。黃秋雨是知名畫家,是讀書人,不斷地購買書與畫,對他來說是非常必要的事情。儘管已經結婚多年,但身為妻子的金婉卻根本就沒有弄明白這一點。單這一個細節,就已經充分地凸顯出了他們之間深深的精神隔膜。而且,從語言的運用層面來看,與小說其他部分的典雅形成鮮明對照的,就是金婉語言的粗俗不堪。那樣一種音氣聲口,活脫脫就是一個市民女子的口吻。以上幾位女性之外,與黃秋雨關係密切的還有一位男性形象,即就是他的老朋友作家譚漁。從小說敘事與人物塑造的角度來看,譚漁的存在價值,更多地是要以一種見證者的身份,給讀者提供介紹黃秋雨的基本成長曆程。在譚漁的理解中,黃秋雨是一位精神靈魂的極端孤獨者,是繪畫藝術的不懈追求者。當然,除了這些相關人物之外,與黃秋雨的死亡脫不了干係的,還有他自己其實已經很糟糕的身體狀況。他所服用的藥物,屍體解剖的結果,以及他那總是頭疼不已的身體症狀,都說明他確實已經罹患不治之症。
然而,到底黃秋雨的死因如何,小說終歸還是沒有做出明確的交代。儘管說命案最終以黃秋雨絕望自殺而作結,但這樣的一種結論很顯然是不可靠的,是某種權勢強力影響的結果。從敘事層面來說,作為一部借用偵探小說外殼的作品,黃秋雨的真實死因,一直是推動故事情節演進的根本動力。米慧以及米慧曾經的戀人羅旗、父親米食堂,那位後來被車撞死的陸軍以及市委書記陸浦岩,也都有著謀殺的可能。自然,身受疾病折磨的黃秋雨自己,也不能說就沒有一點自殺的可能。儘管說黃秋雨的命案最終被定性為自殺,但實際上,擁有豐富偵探經驗的方立言,卻對這個結論有著強烈懷疑:“因為在黃秋雨的命案中,還有太多的疑問,沒有找到準確的答案。比如陸軍手機的來處,並非像他妻子所說那樣簡單,還有黃秋雨被盜的日記,至今仍沒有下落,那才是黃秋雨命案最關鍵的線索。”顯然,墨白在《手的十種語言》中所採用的是一種以建構的方式解構的敘事模式。所謂“以建構的方式解構”,就是說敘述者方立言一方面確實在不斷地進行一種建構的工作,在不斷地設定黃秋雨的死因,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處在一種不斷自我否定的狀態之中,不斷地以一種自我解構的方式否定自己此前的自我建構。以至於關於黃秋雨的真實死因,到最後,也還是一團解不開的迷霧。在我看來,墨白《手的十種語言》的先鋒性,最突出地體現在“以建構的方式解構”這樣一種基本敘事方式的熟練運用上。其實,認真地想一想,小說中給讀者留下的待解謎團,確實很多很多。這裡且以米慧為例略加分析。其一,在黃秋雨留下的手稿中,曾經提及米慧是一個身負命案的女孩子。其二,米慧在信中,曾經一再強調自己要自殺。其三,按照譚漁的說法,米慧其實並沒有死,而是獨身前往深圳了。正因為如此,所以他的父親米食堂才會去千里尋女。那么,米慧到底有無命案在身?她最後到底是自殺身亡,還是遠走深圳了?諸如此類的敘事謎團,敘述者在文本中都沒有給出明確的交代。有一點不容忽視的是,墨白通篇所採用的,實際上都可以被理解為一種不可靠敘述。細讀文本,即不難發現,無論是黃秋雨留下的手稿,還是相關當事人的敘述,從根本上說,也都只是立此存照有此一說而已。這些關於事實真相的言說,究竟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虛假的,敘述者均無交代。或者說敘述者方立言的偵探身份本身,就決定著他不可能給讀者提供一種可靠的信息。我們之所以斷言墨白的小說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偵探小說,根本原因正在於此。因為他只是若干蛛絲馬跡的觀察與發現者,至於這些蛛絲馬跡最後能不能被證實或者證偽,顯然還需要再加以特別的敘述交代。假若是真正意義上的偵探小說,到最後都要把這些疑團交代清楚的。但墨白的志趣卻顯然並不在此。墨白所一力堅執的先鋒小說,乃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小說本身愈模糊愈具有藝術層面上開放性,小說的先鋒性也就愈強。
實際上,墨白這部長篇小說的真正藝術聚焦點,並不在所謂黃秋雨的命案本身。藉助於對於黃秋雨命案的勘探偵破,極其有效地切入到黃秋雨複雜的精神世界之中,對於黃秋雨的精神世界做出深度的挖掘與表現,恐怕才是墨白最根本的創作意圖所在。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敘述者方立言在偵破黃秋雨的命案,莫若說他是在深入探究表現著知識分子黃秋雨的精神世界。應該注意到小說中談論黃秋雨的繪畫作品“手的十種語言”時的這樣一句話:“他之所以這樣,就是要讓人們明白,他這是對關於人類精神的探索,是要進入人的靈魂。”這樣的話語顯然是墨白的一種夫子自道,他之所以要用黃秋雨系列畫作的名字來為自己的這部長篇小說命名,根本原因顯然也是要探索人類精神,“要進入人的靈魂”。探究誰的精神世界呢?最主要的,當然還是小說的主人公黃秋雨。那么,黃秋雨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形象呢?是一個情聖還是花花公子?是一個藝術的殉道者還是一位功利之徒?是一位欲望的狂熱迷戀者還是一位精神的痛苦探求者?都可能是也都可能不是。是有是的道理,不是更有不是的道理。在小說後記中,墨白曾經這樣談論過黃秋雨這個人物形象:“當我面對黃秋雨留下的文字時,我就像看到了一個精神病患者,一個神秘幻想者,一個精神流浪者,一個現實生活的夢遊者,一個癌症病患者,而更多的時候,他是一個有著痛苦的靈魂、有著非凡創造力的藝術家……”墨白對於黃秋雨的說法,是不是就可以被當做黃秋雨精神世界的最終定位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道理說來其實也非常簡單,對於墨白這樣的先鋒作家來說,反對一種定於一的終極結論,是他們更為根本的藝術理念。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墨白所有的先鋒小說創作,都在致力於對於定於一這樣一種思維習慣的顛覆與消解。既然如此,我們也就只能把墨白自己的說法作為眾多的理解之一種來看待。事實上,正如同墨白所採用的那樣一種以建構的方式解構的敘事策略一樣,關於知識分子黃秋雨精神世界的理解與判斷,我們到最後也不會得出一種定於一的明確結論來。假若說黃秋雨的生命歷程本就是一種生命展開的過程,那么,我們對於黃秋雨這一形象的闡釋與解讀,恐怕也在一種永遠的過程之中。
墨白《手的十種語言》藝術先鋒性另外一個突出的特徵,就是對於多種藝術形式的積極徵用與有機整合。這裡面,既有黃秋雨遺留下的手稿,信件,也有相關當事人寫給黃秋雨的信件。既有譚漁的深情回憶文章,也有留存下來的匯款單據。既有黃秋雨與相關當事人的詩歌,也有別人對於這些詩歌的評論文章。既有新聞報導,也有新聞報導的相關資料。面對著如此一種具有後現代拼貼藝術效果的藝術審美景觀,墨白說,自己已經“迷失在了具體的文本語境之中”。實際上,文本語境的迷失者又何止是墨白自己呢?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這些所有試圖進入墨白小說世界的人們,也都可以被看做是墨白自己所建構的小說藝術迷宮中的自覺迷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