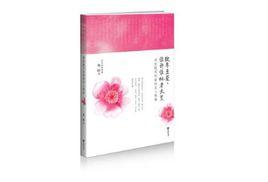圖書簡介
《彼年豆蔻,誰許誰地老天荒:那些隨風而逝的名人情殤》是作者六年的心血文集。在這六年的時間裡,作者查閱了海量的歷史資料,用感性、唯美、清麗的文字,寫下了諸多古今中外名人的愛情故事,以期讓讀者在唏噓感嘆甚至淚雨漣漣里感受這些名人的愛情。這些作品曾先後發表於《意林》《讀者》《百家講堂》《青年文摘》等,得到了大量讀者強烈的反響。
目錄
錯過
那個時候的我們,天真地以為,那只是一段情,走過之後才明白,其實,那是一生。許多時候,一轉身,就是一輩子,只可惜我現在才懂。
003 / 張茂淵:愛過半個世紀
007 / 呂碧城:醉笑陪君三萬場
011 / 陳岱孫:被歲月覆蓋了的花開
014 / 蘇曼殊:半緣修道半緣君
024 / 梁啓超:第一知己總讓卿
宿命
也許,一切的一切,是生命的輪迴中該有的劫,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一如,撲火是飛蛾的宿命。
033 / 李煜:蓮花台畔蓮花落
038 / 普希金:誰念西風獨自涼
044 / 黛安娜:童話里有朵雨做的雲
052 / 傅雷: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063 / 秋瑾:鑑湖女俠的詩意人生
070 / 小野洋子:殤花盛開
077 / 弘一大師:菩提樹下的紅塵戀
081 / 蕭紅:一路逃亡,一路愛
嘆息
過往的歲月里,她(他)一直將頭深深地低進塵埃里,可是,至死,她(他)都沒有等到與他(她)攜手的前世今生。
089 / 金岳霖:你是我的四月天
096 / 杜拉斯:愛到無人能懂
101 / 勃拉姆斯:43年的花開無聲
110 / 卡夫卡:死神面前的愛情舞蹈
114 / 潘玉良:情到深處無怨尤
119 / 奧黛麗·赫本:1954年的蝴蝶胸針
煙花
那些無法牽手一生的愛情,終如綻放的煙花,熾熱、美麗,瞬間的璀燦過後,留下無盡的黑暗與蒼涼。
127 / 葉賽寧:我為愛你而來
133 / 步非煙:不過是一場風花雪月
138 / 陸小曼:煙花戀
148 / 居里夫人:瑪麗的愛情
152 / 薩特·波伏娃:塞納河畔凋零的風鈴草花
頹敗
每個男人的最初,都有一個櫻花般的純白女子,如天使般飄零在他生命的最深處,注定頹敗。
163 / 吳冠中:那時花開
170 / 小鳳仙:你曾是我生命里的天使
177 / 諾貝爾:殤情諾貝爾
185 / 莫泊桑:莫泊桑的“魂斷藍橋”
192 / 柴可夫斯基:13年的柏拉圖
200 / 葉芝:與愛,痴纏一生
205 / 雨果:雨果愛情世界裡的傷情女人
齏粉
那些曾經做出的,以為堅如磐石的承諾,最終,在風馳電掣的時光中,化為齏粉。
213 / 阮玲玉:愛情是一襲華美的袍
218 / 唐婉:疑是驚鴻照影來
223 / 拿破崙:有多少愛,可以重來
228 / 飯島愛:性很近,愛很遠
231 / 芭芭拉:誰人真愛芭芭拉
238 / 梅蘭芳:如果愛,請深愛
245 / 費雯麗:亂世佳人亂世情
零落
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如水的溫情和雙眸間灼灼的期待,都已隨風成塵,最終,分散在時光的長河裡,零落成一場眼淚的狂歡。
257 / 陸徵祥:人生若只如初見
263 / 白朗寧:有一種殤,叫情深不壽
272 / 三毛:夢裡花落知多少
280 / 巴金:今生只為你動情
288 / 傑奎琳:風中的傑奎琳
293 / 于鳳至:大愛至簡
296 / 老舍:茶館裡的情感人生
304 / 林覺民:不負天下不負卿
311 / 鄧稼先:彼年豆蔻,誰許誰地老天荒
序言
因為愛,所以執著
想來,我與文字的緣分,應該是與生俱來的。此刻,當我為自己人生的第一本書作序時,發現生命里所有或諧趣或溫暖或執著或滿足的記憶竟都與文字有關。
5歲時,常常地,一個人,站在老屋前的池塘邊,面對那一泓碧波蕩漾的春水,極度興奮地用不同的聲音大喊著:
“空氣在顫抖,仿佛天空在燃燒。”
“是啊,暴風雨就要來了。”
“你像一個真的游擊隊員一樣打死了德國士兵,你的委員會裡還有誰懷疑你不是瓦爾特呢?”
《瓦爾特保衛塞拉耶佛》,那是我一個人的電影,在這部電影中,我一個人扮演著包括康德爾、迪特里施、比肖夫等人在內的所有角色。
彼時,哥哥有一個上了鎖的抽屜,抽屜里珍藏著幾本小人書和一摞信紙,哥哥對它們視若珍寶,任誰動一動他都會與之拚命。
一次意外,我發現如果將旁邊那個沒上鎖的抽屜拉出來,將手伸到最裡面,竟然可以從哥哥抽屜的空隙中將最靠邊的一本小人書拿出來,於是,從那一刻起,哥哥前腳去上學,後腳我便把小人書偷出來,跑到村頭讓看麥苗的江阿姨給我講小人書。
江阿姨是個上山下鄉的知青,身體虛弱,村長照顧她讓她在村頭照看麥苗地,以防村民們家裡養的雞啄食剛剛返青的麥苗兒。
一次兩次三次,半個多月後,當我氣喘吁吁地跑回家想趕在哥哥放學之前將小人書放回原處時,被因考試提前放學的哥哥抓了個正著。
於是,那一日,我和哥哥兩個人都哭了個昏天暗地,我是因為挨打,哥哥是因為心疼他那被翻得捲起了毛邊兒的小人書。
那本小人書,讓我第一次知道了文字世界裡的精彩,也正是從那時起,努力識字,去縣城的書店裡蹭小人書看成了我整個童年裡最幸福的事。
17歲,去外地讀中專,在學校的圖書館裡,真正領略到了什麼是“浩瀚的文字海洋”,無數個夜晚,宿舍已經熄燈,同學們沉沉睡去的時刻,站在走廊盡頭的樓梯後,捧一本書,借著樓道里昏暗的燈光,一個人獨自在作者筆下的故事裡流連。
19歲,我的文字第一次變成了鉛字,沒有樣報,有的只是市晚報社寄來的一張淡綠色的稿費單,拿著那張稿費單,想著一個又一個陌生人閱讀著自己的文字,那種歡喜,真的是夢中都會微笑。
30歲,已結婚生子、在一家事業單位做了七年會計的我忽然就有了放棄工作專職寫作的衝動,全家上上下下,除了愛人沒有一個人支持我的這一決定,尤其是公婆與爹娘,何止是大惑不解?簡直是暴跳如雷。於他們而言,放棄工作離開“組織”的懷抱根本就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幾位老人輪番轟炸,先是苦口婆心,繼而大發雷霆,發展到最後幾近歇斯底里。
然而,對文字的熱愛已經讓我到了欲罷不能的地步,再一次地,我的那種撞了南牆也不回頭的個性凸顯,一句“我寧肯吃糠咽菜,也不想等將來老了,躺在床上,行將就木時,再去後悔一生所過的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話,讓幾位老人頓時沒了脾氣,於是,雖然受到了重重阻隔,最終還是辭了職。
從此,各種文字,日日夜夜地,在心底自由地歡唱。
每日裡,或是坐在電腦前十指翻飛,或是捧一本書,半倚在陽台的長椅上靜靜地讀,於是,從此也便有了文字的魅惑,用自己的文字去魅惑他人,亦或是在他人的文字里被魅惑得或喜或悲。
說不清從何時起,竟愛上了那沉寂的夜,喜歡在黑暗中放縱自己的思緒,在文字中放肆地妄想那些塵世間並不存在的悲歡離合。多少次,看著那一個個文字在自己的指尖上跳動,不由自主地,情感隨著故事裡的情節起起伏伏,此時,思維是活躍的,心是溫潤、細敏的。哪怕,是寫下一個悲情的故事,在將自己感動得淚雨漣漣之後,竟仍有一種拋下生活重負、自由舒展翅膀的快樂感覺。
第一次接觸名人的愛情世界是在2005年,彼時,從網上看到一段寫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的文字,為那個女人那份隱忍到讓人心疼的愛情深深地感動,很快,一篇《愛過半個世紀》便刊發到了《遼寧青年》上,讓我萬沒想到的是,這篇只有2000字的文章,竟然先後被《讀者》《意林》《特別關注》《文苑》等數家知名雜誌轉載,並且,讀者反應非常強烈,
後來,我又陸續寫了幾篇這樣的名人愛情稿,竟都收到良好的效果。
2008年,《青年文摘》雜誌發表了我寫的格里高里 ·派克與奧黛麗·赫本的情感文章《1954年的蝴蝶胸針》,讓我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雜誌一上市,短短几天內,轉載此文的網頁便達到了數百頁,只在派派網上,便有十幾名朗讀愛好者選中了這篇文章,在赫本的百度貼吧里,讀者更是留下了一條條讓人激動不已的評論:
“當我看完這文章時,已淚流滿面。”
“這是唯一使我感動落淚的關於愛情的文章。”
“今天看到,我流淚了,終於知道什麼是愛情。”
“看完之後,心在顫抖,淚在翻騰。”
“我是在《青年文摘》上看到這篇文章的,當時讀第一遍,已經是泣不成聲了。”
“我在教室里,忍住,不能哭。”
……
太多的讀者的眼淚讓我心潮澎湃,從那一刻起,寫這樣的一組愛情文章,出一本《名人情殤》的書便成了內心無法壓抑的衝動。
於是,接下來的幾年裡,新浪讀書、騰訊讀書、百度文庫、圖書館、書店成了我每日必定要光顧的場所。
彼時,我已經開始了生命中最初的、居無定所的北漂生活,當時住在東交民巷,常常地,一個人步行到前門,坐一個多小時的特 4公車去國家圖書館查資料,有時,國家圖書館裡沒有的,便到各大書店或網店裡去淘。每日裡,我所做的,便是將自己埋頭書中,在前人的愛情故事裡沉溺流連,樂此不疲,一任朝來暮往、雲捲雲舒。
時至今日,我依然清楚地記得,此前,一個相識多年的老友寫過一篇有關倉央嘉措愛情的文章,因我看到的資料與她訴講的內容相距甚遠,我懷疑朋友寫的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的愛情與歷史事實不符,為了給自己的讀者還原一段真實的歷史,我曾跑遍了西單圖書大廈、中關村圖書大廈、甜水園、地壇書市、三聯韜奮圖書中心等地方,奔波了二十多天,終於,
綜合各種資料,並結合作家高平撰寫的、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的《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一書,完成了《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的絕世情殤》一文。
常常地,幸福於那樣的感覺,夜闌更深時,一個人獨自坐在電腦邊,思緒不由自主地飄回到歷史深處,將那些被世人或遺忘或丟棄了的、卻無意間感動了自己的愛情故事,輕輕地撿起,將她或他的或驚心動魄或靜如止水的情感,默默地展開、細品,然後,像個極敬業的紡織女工般,以文字為梭,將那些散落在風中的碎片一一地串聯起來,讓那些在歲月里老去的或纏綿或悽美的愛情,在自己的指尖兒上,如梵谷筆下的向日葵般,于波瀾不驚中,絢爛而溫暖地盛開。
從2005年初至2011年末,創作此書的6年間,人是奔波的,心是快樂的。哪怕是後來由於愛人工作的關係搬到昌平燕丹巷那狹小的連個客廳都沒有的居室里,日日過著麵包、速食麵果腹的生活,因了有了文字的一路陪伴,心亦是明淨快樂的。
可以住地下室,可以啃涼饅頭,可以穿最廉價的衣服,但生命中不能沒有文字,這便是我一直以來堅持的生活理念。正如一位朋友所說,“ 一個人愛文字愛得緊了,世間所有的苦難與功名利祿都將變得無足輕重,唯有文字,才是生命中最真切的、最不能割捨的一環。”
2008年之後,物價的高起引發生活成本的巨增,巨大的生活壓力使得與我一同出道的朋友們紛紛改行,只剩下包括我在內的少數撰稿人依然固執而絕決地將自己的生命留在了文字里。我不會離開,而且此生無論遇到什麼都不會離開,因為只有在文字里,我才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那種生命輕舞飛揚的快樂感覺。
有書可讀,可以讓自己的心靈在文字里肆意地盛開,可以讓自己沉湎在那些靈秀的文字中一點點地老去,也許,我一生所要的幸福不過如此吧。
張愛玲說:“有美的身體,以身體悅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悅人。 ”我此生要做的,便是:“有美的文字,以文字悅人。”
如果,我的讀者,因了這些文字,而笑、而哭、而理性地對待婚姻與一份遲來的愛,我將知足。
最後,對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曾玉立編輯、北京鳳凰天下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的京華浪客編輯、北京時代華語圖書有限公司的梁珍珍編輯以及所有為此書提出來意見與建議的朋友們真誠地道一聲“謝謝 ”,謝謝你們的鼓勵與支持,謝謝你們一路走來所付出的辛勤與汗水,願在文字的人生旅途中,我們能一起攜手並肩,越走越遠!
硃砂,2012年 7月於河北滄州
樣文
樣文1
愛過半個世紀
孑然一身50年,78歲才成為新娘;半個世紀的等待,只為,那曾經的一場愛。如此曠世奇緣,其主角究竟是個怎樣超凡脫俗的人兒?
她叫張茂淵,外祖父是晚清重臣李鴻章,侄女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才女張愛玲。她留過洋,集萬貫家資、容貌才情於一身,她的愛情,波瀾不驚卻又另人唏噓感嘆。
他們是彼此的初戀。
1925年,25歲的張茂淵在開往英國的輪船上遇到了英俊才子李開弟,女兒的心事,象春日裡的花苞兒,風一吹,便開了。
26歲的李開弟對張茂淵亦是一見鍾情,甲板上,李開弟深情的用英語為張茂淵朗誦了拜倫的詩。
故事至此,原本應是一段才子佳人的人間佳話。然而,及至李開弟了解了張茂淵的出身後,熾熱的情感忽然就冷淡下來。在李開弟這樣一個熱血男兒的眼裡,張茂淵的外公、與洋人簽署了《馬關條約》的李鴻章是個民族敗類;張茂淵的父親,馬尾一戰中狼狽逃竄的張佩綸是個懦夫,而張茂淵的哥哥又是個打嗎啡、嫖妓的浪子,這樣的一個貴族人家的閨秀,必是嬌如嬰兒,弱如溫室花草,怎配和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雙棲雙飛?於是,李開弟毅然斬斷了與張茂淵的情絲,蒼促中和一位女留學生結為連理。
張茂淵應邀參加了李開弟的婚禮,那一刻,她將一個女人的內斂發揮到了極致。面對新娘,張茂淵神泰自若,落落大方,仿佛自己和新郎間從未有過感情的瓜葛。沒有人知道,此刻,張茂淵平靜的表情下,痛苦是何等鐵馬冰河般的洶湧?!
然而,另李開弟萬沒想到的是,張茂淵非但不是一根只會依附大樹的藤、不是《紅樓夢》中相信宿命、任人擺布的迎春,恰恰相反,接受過西方教育的張茂淵性情堅毅如賈府中的探春,有著一顆男兒一樣的雄心,她自強自立的品性與她的家族格格不入。
了解了張茂淵為人個性的李開弟象尤三姐自刎後的柳湘蓮,苦惱,悔恨,深深的自責。
錯過一個人最可怕的方式是,你就在他(她)身邊,卻知道已不能再擁有他(她)。此時李開弟的妻子已有身孕,張茂淵和李開弟都是看不得別人痛苦的人,兩個人的戀情,注定成了開在傷口上的一場煙花,愛雖真,卻隔了一條無法泅渡的河。
如此也便不難理解,張愛玲在香港讀書的三年中,李開弟為何象對待親生女兒那般照顧愛玲,箇中原委,又何償不是把愛玲當成了對張茂淵情感的寄託?
許多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感情有時只是一個人的事,愛與不愛只能自行了斷。張茂淵,這個高傲清冷型的女子,自李開弟結婚後,便再也沒愛過別人,只守著父親留下的一份家業過活。
張茂淵說,今生等不到你,我等來生,神情語氣中的決絕讓人驚心動魄。
若記一個人一生一世,那定是需要一份平絕的勇氣和一縷化不開的濃情。也許李開弟只是這個世界上的一個人,但對於張茂淵來說,他卻是整個世界。
心若知道靈犀的方向,哪怕不能朝夕相伴,亦是一幅最悽美的風景。於是,在長達半個世紀的等待里,張茂淵和李開弟這對有情人,隔塵相望,不越雷池半步。人們看到的,不是心頭碎裂的傷,徹骨的思念以及等待的絕望,而是一份淡定從容,一份靜靜的守候。在生命的角落裡靜靜開著的,那些寫著初戀的花,是只有一個人才懂的幸福呵。
十年浩劫中,年近古稀的李開弟被打成反革命,每日在弄堂里清理垃圾,親友避之唯恐不及。彼時的張茂淵已是家財盡散,卻仍就隔三岔五的從自己並不富裕的供給中擠出一些,接濟李開弟。每每去看他,張茂淵總是捋起衣袖,捲起褲管,用她從小彈鋼琴的手,接過力不從心的李開弟手中的水桶掃帚,幫他“改造”,做那些笨重的粗活兒。此時的愛,已無需言語,舉手投足間的一切,他(她)能懂,也只有她(他)懂。
及至李開弟的老伴去世,張茂淵已經78歲,終於如願以償地和自己初戀的人兒走到一起。時間已將無數個事件潤澤成珠,保存下來,留給兩個相愛的人兒,一起在黃昏里細數,哪些是雲捲雲舒下淡淡的喜悅,哪此是車馬喧囂聲中思念的悠長,還有,那些紅塵往事與年輕過的容顏。
張茂淵90歲時去世,用50年的執著,換來了12年的相依。
50的等待是漫長的,正是因了這份漫長,兩個相愛的人兒才更加珍惜相依的時光,同時也正是因了這份姻緣的來之不易,兩個人才真正懂得,如何用心去體悟那份遲到的幸福和美麗。
=================================================================
樣文2
菩提樹下的紅塵戀
那樣的一個女子,似哺育了她的富士山一般,有著寧靜而熾熱的美。她的人,溫良謙恭,心性似她的名字纖塵不染,雪子,生於十九世紀末的扶桑女子,和所有二八的女兒一樣,在澀如綻蓓的錦秀年華里,無數次的,於盈盈的燭光中,許下最純真的愛情夢想。
或許,真的是老天有眼啊,她的祈願在那一年終於成真。慈悲的佛祖讓她於千萬人中,遇到了那個叫李叔同的中國男人。四目相對的一剎那,他那由豐富的人生閱歷積累下來的洞析人生的睿智眼神瞬間便捕獲了她的芳心。他比她大許多,並且,在故國家園裡有妻有子,然而,她依舊愛了,義無反顧。
那個男人簡直是個天才,音樂、詩詞歌賦、篆刻、書法、繪畫、表演幾乎樣樣精通,像所有那個年代懷了一腔熱忱卻報國無門的熱血青年一樣,他追隨他心中的領袖蔡元培,想闖出一條救國興邦的康莊大道,然而,不幸的是,蔡元培遭人迫害,被當局通輯,做為同黨的他亦難逃劫數,於是,無奈之下,他東渡日本,學習西洋油畫與劇本創作,將滿腔的悲憤和一身的才情,埋藏在沉默的丹青與跳動的音符間。
彼時,他是她家的房客,日夜在同一屋檐下相遇,久而久之,她入了他的畫,他入了她的心。
她灼烈熾熱的愛,溫暖了一騎飄在異鄉的遊魂。她愛他,為了他,她不惜赴湯蹈火。而她對他,卻索求不多,一份真實的感情,一掬茅檐低小的簡單快樂,足以慰平生。然而她愛的這個男人,卻不是可以樂不思歸的蜀主劉禪,在他的世界裡,家衰國落的痛,像一塊經年的疤,於每一個陰天返潮,一次次地,將蝕骨的悲涼泌入一顆遊子的拳拳愛國之心。
6年的相依相伴,他們在一起度地了一生中最靜美的愛情時光。她期盼就這樣廝守到終老,然而她不知,他的心無時不繫著他的祖國。
辛亥革命的成功,讓一心報國的他再也無法在異國他鄉的溫柔里消蝕青春的大好年華,他回來了,帶著一腔的熱情與滿腹的經綸回到了那片生養了他的土地上。他填《滿江紅》的詩,為共和歡呼,他主編《太平洋報》,倡導精銳的思想和嶄新的文化,長久壓抑的生命在這片理想的樂土上重新豐潤開來。
有愛不覺天涯遠,她隨著他,也來了。她告別了那滿樹的櫻花,來到這陌生的國度,一任他的世界一天天開闊而自己的世界一天天萎縮下去。
她不怨他,她愛他,她尊重他的選擇。她站在那個男人的身後,把頭深深地低進了塵埃里。為了他,她甘願在這異國他家忍受寂寞與孤獨,只為心中那一紙執子之手與子攜老的的愛情之約。
然而,他的熱情與她無怨無悔的付出並未得到時局的認同,軍閥割據的殘酷現實讓他不得不在報紙被關閉後移師江浙。
又一次地,她跟了他,亦步亦趨。他就是她的家,有他在,她便是幸福快樂的啊。
他在學堂里教書育人,培養了一代名畫家豐子愷與一代音樂家劉質平等文化名人。他仰慕佛法之宏大,喜歡清燈古佛相伴的寧靜,於是,終於在某一日,他拋卻了紅塵,至虎跑寺斷食十七日,身心靈化,遁入空門,法號弘一,從此一心向佛,普度眾生。
從滿頭青絲綴落的那一刻起,他便從榮華富貴中抽身而去,俗世所有的絢爛都化做了脫俗後的平淡,而他對她的小愛,也必將從此轉變成了對天下蒼生的大愛。
她愛他敬他,可她的內心卻還沒有強大的可以靜如止水的目送著愛情的離去。她淚流,百思卻找不到答案。她不捨,她不服,追至他剃度修行的地方。於是,那一晨的西子湖畔,兩舟相向時,便有了這樣的一段對話。
她喚他:“叔同―――”
他駁她:“請叫我弘一。”
她強忍著滿眶的淚,“弘一法師,請告訴我,什麼是愛?”
他回她:“愛,就是慈悲。”
他不敢看她,想來,他也是怕了,怕她那雙朦朧的淚眼會勾起昨日的種種你儂我儂,擾了自己那顆歸依佛門的淨心。
她固執而絕望的看著他的眼睛,心底的疼痛,象秋日的湖水,柔軟綿長,涼意無限。
他的身影消逝在蒼茫的霧氣里,甚至,沒有道一聲珍重。她悲傷的無又復加,她知道,不過是一個轉身的距離,從此,便注定紅塵相隔。她的愛,她的哀,她的悲,她的淚,從此都已成為了這段愛情最後的華章。
一輪明月耀天心,無奈零落西風依舊。
放棄了塵世之愛,菩提樹下的人生,注定將更為宏大豐厚:新文化的先驅、藝術家、教育家、思想家、第十一代律宗世祖……,那個男人的生命達到了世人無法啟及的高度,而我卻在他圓寂前寫下的“悲欣交集”的四個字里,分明聽到了一個扶桑女子碎心的呤誦: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
===================================================================================
樣文3
1954年的蝴蝶胸針
他是個紳士,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男人,有著雕塑一般堅毅的輪廓和剛直不阿的個性。他舉止優雅,氣質謙和,純淨的眼神象個莊嚴的傳教士。他能將笑容演繹得讓人心動,柔腸百轉而又分寸在握。他是全球數以千萬計的女人們的夢中情人,他的生命里有無數俏顏佳麗走過卻沒有出現過一次緋聞。在過去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光里,他一直被全世界的影迷們做為偶像與道德榜樣崇拜著,他的名字叫格里高里*派克。
她是個天使,出身名門,會講五國語言,舉止優雅得體,氣度非凡。她高貴善良,與世無爭,柔媚嬌羞得象個不諳塵事的孩子。她的性格矜持內斂卻又平易近人。她有著姣美的容顏和如花般的笑靨,兩隻會說話的大眼睛如一泓高原的碧潭,清澈靜謚,楚楚動人,長長的睫毛象秋日裡飛舞的蝴蝶,薄如紗翼的翅膀扇動著青春的快樂與輕盈,她的名字叫奧黛麗·赫本,
纖塵不染的豆蔻年華里,天使遇到了紳士,在浪漫之都羅馬的那個假日裡,一段塵世間最純美的愛情悄然萌生。
那個時候的他,已是全世界盡人皆知的明星,剛剛過完36歲的生日,而當時的她卻只有23歲,還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女孩兒。她是他的影迷,對他有著近乎痴狂的崇拜,當她第一次見到他時,她甚至激動的說不出話來。
他亦如此。
看到她的第一眼,他的心忽然就動了一下,一股異樣的情愫從心底悄然湧起,感情象海潮剛剛退去的沙灘,柔軟而溫潤。
眼前的女孩兒,敏感而脆弱,不為人知的心事蘊藏在美麗的大眼睛裡,安靜而憂傷,讓人陡生憐愛。那一刻,他分明感覺到了一個微妙階段的開始。
那場戲裡,他們分別飾演男女主角,忙裡偷閒時,兩個人便到河邊散步,涓涓流淌的河水竊聽著這對人兒的喃喃私語。
他喜歡看著她,眼神里蘊滿了可以讓人融化的憐惜。她也喜歡和他在一起,聽他說話,看他微笑。偶爾,她會將自己冰冷的小手放進他寬厚的掌心裡,感覺著來自那個敦厚男人的溫暖。
那個時候,他的婚姻已經走到了盡頭,他多么渴望得到她的愛情啊,可是,他不是個善於表達的男人,看盡了世事蒼桑的他已經習慣了將所有的喜怒哀樂都掩藏在波瀾不驚的表情之下。
她愛他,可是,她不敢說。她很清楚,身邊的這個男人,他是別人的丈夫,是三個孩子的父親。幼年時破裂的家庭陰影以及她所受的教育讓她對他望而卻步,善良如天使般的她怎么忍心讓自己愛的翅膀沾染上別人濡濕的記憶?!那個夏日,她的愛,在他的笑容里,一次又一次熱烈而絕望的盛開。
許多時候,一朵矜持的花,總是注定無法開上一桿沉默的枝椏。於是,一段故事在那個夏日嘎然而止,再也沒有後來。
《羅馬假日》的公映,讓她一夜之間從一朵山野間羞澀的雛菊變成了鎂光燈下耀眼的玫瑰。很快,她有了愛情,梅厄·菲熱,好萊塢著名的導演、演員兼作家,他的朋友,他介紹給她的。他很欣賞那個男人的才華,希望那個男人的職業可以帶給她更大的成功。
果然,那一年,她的事業和愛情雙雙豐收,她獲得了當年的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並且,和梅厄走進了婚姻的殿堂。
他參加了她的婚禮。
他還是那樣溫厚而寬容,用平靜的微笑應對著眼前的一切。沒有人知道,他不露聲色的外表下,掩藏著的,是一種叫做無奈和認命的東西。
做為禮物,他送給了她一枚蝴蝶胸針。
那是1954年,愛情於他和她,是開始,也是結束。
那個時候的她,天真的以為,自己一轉身,便可以躲過千萬次的傷心,可是,她卻不知道,如此,也便錯過了一生的風景。
她結婚後不久,他便離了婚,然後又結婚,再次成為了別人的丈夫。
想來,男女之間的交往確實是很玄妙的,從友情到愛情僅一步之遙,但從愛情回到友情,卻仿佛要經歷千山萬水。試問,塵世間,當愛情華麗轉身,還有幾個人能心懷坦蕩的重擺友情的宴席?可是,他們做到了,憑藉著對緣份的尊重和對友情的信仰,兩個人將千山萬水的距離濃縮成咫尺天涯,將所有的愛與情埋藏在了那個夏天的《羅馬假日》里。
許多時候,天使之所以被稱為天使,不僅僅是因為她們擁有天使的氣質,更重要的,是她們擁有了愛的天堂。而如果沒有了天堂,再美麗的天使也終將被世俗喧囂的塵埃覆蓋。後來的事實表明,她的天堂,不是梅厄,而是他,是格里高里*派克那溫暖的目光。後來,她又演了許多部電影,雖然她依舊是那個優雅美麗的女子,可眉宇間卻隱約多了一絲掩飾不住的寂寞。
梅厄的移情別戀,給了渴望一份愛情至終老的她一個致命的打擊。她離了婚,後來,又結了婚,又離了,再後來,一個又一個的男人,從她的生命里,兜兜轉轉,走近又走遠。四十年的光陰里,一承不變地陪在她身邊的,只有那玫蝴蝶胸針。
無數次的,她給他打電話,說到傷心處,忍不住淚雨漣漣。他輕聲的安慰著她,說一些無關痛癢的話。沒有人知道,於他而言,她的每一滴眼淚,都如一枚跌落的彗星,刺入大海的心房,表面風平浪靜,內心卻已是鐵馬冰河般的洶湧。
她至死都不知道,從他遇到她的那一天起,她便一直是他生命里的白月光,日日夜夜地,燦爛在他心靈的最深處。
1993年1月,天使飛回了天堂。
他來了,來送別她,看她最後一眼。
彼時,他已是77歲高齡,拄著拐仗,步履蹣跚。
花叢中的她,微闔著雙眼,象一株夏日雨後的睡蓮,純潔而安靜。
歲月蹉跎了她的容顏,人們看到的,是美人遲暮的悲涼。而在他的眼裡,她依舊是那個嬌小迷人,眼裡流溢著無限哀傷的女孩兒。他輕聲地喚著她,她卻不回答。她聽不到了,永遠聽不到了,白髮蒼蒼的他久久無語地看著她,老淚縱橫。
送別她時,他低下頭,輕輕地吻了一下她的棺木,咽嚅著:“你是我一生最愛的女人。”
他終於說出了埋藏在心底的那句話,那是她一生都想要的,可是,它遲到了,遲到了整整40年。此時的他亦不知道,過往的歲月中,她一直將自己的頭深深的低進塵埃里,可至死,她還是沒能等到與他攜手的前世今生。
十年後,著名的蘇富比拍賣行舉行了她生前衣物首飾的義賣活動。
又一次地,他來了,顫顫巍巍。
87歲的他此行的目的,只為那枚陪蝴蝶胸針。
最終,他如願的拿回了它。
捧著那枚蝴蝶胸針,抽搐的記憶,在時光的隧道里,迅速的流轉,他仿佛又看到了,羅馬假日裡那個美麗善良、不諳世事的小女孩,正一路快樂輕盈的向自己走來……
40年的光陰里,他一直沒有告訴她,自己送她的這件結婚禮物,不是一枚普通的胸針,而是,他祖母的家傳。
49天后,他微笑著閉上了眼睛,手裡握著那枚蝴蝶胸針,就象握著她的心跳,握著無法回頭的歲月和歲月深處那段永不再復的青春之戀。
送別他的那一天,人群舉著鮮花,從四面八方湧來。他的葬禮,通過網際網路,進行了全球直播。那一天,在世界的各個角落裡,成千上馬的影迷們默默祈禱著,祈禱紳士在另一個世界裡,找到天使,還給她一個,在塵世間曾經錯過的天堂。
============================================================================
樣文4
43年的花開無聲
在愛情的世界裡,三人行,必有所傷,這是一條亘古不變的規律。
1853年,當年僅20歲的勃拉姆斯在舒曼的家中遇到舒曼的妻子、比他大14歲的鋼琴家克拉拉時,他便知道,自己將從此陷入一場無望的愛情里。
沒有人曉得,那一刻,一朵叫做初戀的花,在這個桀驁不訓的大男孩兒心中悄然綻放。
勃拉姆斯從小生活在漢堡的貧民窟里,沒有讀過多少書,在他還是個少年時,便為了餬口混跡於酒吧間,上層社會中那些待人接物的繁文縟節於他而言遙遠而陌生。他生性粗獷,脾氣暴戾,凡事都喜歡以武力解決,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血氣方剛的大男孩每每走進舒曼的家中、尤其是見到舒曼的妻子克拉拉時,便象換了一個人似的,瞬間變得謙虛儒雅起來,這不能不說是愛情的力量。
彼時,集作曲家、音樂評論家、鋼琴家於一身的羅伯特*舒曼在德國甚至整個歐洲早已是盡人皆知的人物。當勃拉姆斯坐鋼琴前,取出他最早創作的一首C大調鋼琴奏鳴曲的草稿、輕靈的十指一路掠過黑白相間的琴鍵時,一向沉穩含蓄的舒曼忍不住高呼:天才啊,年輕人,天才!
當即,舒曼興奮的提起筆,在自己創辦的《新音樂雜誌》上,寫下了一篇改變了勃拉姆斯一生命運的著名評論《新的道路》,由此,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開始在音樂界嶄露頭腳。
2:
勃拉姆斯從小生活的環境讓他鮮有機會接觸有教養有風度的人,尤其是年輕的知性女人,在他的的眼裡,美麗、智慧、集才貌與光環於一身的克拉拉,象水墨畫裡的一抹嫣紅,鮮明的讓人觸目驚心。彼時的他做夢也不會想到,眼前這個碧人兒日後竟然會成為一個前半生被命運垂青後半生卻被命運詛咒的不幸女人。
舒曼的妻子克拉拉出生在一個鋼琴世家裡,父親維克是其丈夫羅伯特*舒曼的鋼琴老師。從5歲起,克拉拉便跟著父親學習鋼琴,13歲開始登台演出,其音樂天賦受到了當時著名音樂家李斯特的高度評價。
1828年,在大學裡攻讀法律的舒曼住進克拉拉的家中,師從克拉拉的父親維克學習鋼琴時,彼時,年僅9歲的克拉拉正在做為天才少女,忙於在歐洲的穿梭演出。
7年的朝夕相處,愛情在這對年輕人的心中潛滋暗長。
1835年,舒曼與克拉拉私定終身。不料,他們的愛情卻遭到了克拉拉父親的堅決反對,經過11個月漫長的法律訴論,最終,有情人終成謄屬。
做為懲罰,維克將克拉拉和舒曼逐出了家門,從此,兩個人過上了恩愛而艱苦的生活。
在克拉拉的支持下,舒曼在萊比錫創辦了《新音樂雜誌》,向保守、庸俗的舊音樂發起了挑戰,一度,《新音樂雜誌》成了當時德國進步音樂思想的喉舌。
同時,愛情的力量,使舒曼的音樂創作熱情空前高漲,與克拉拉結婚後,短短一年的時間裡,舒曼便創作了138首歌曲。在一首名為《獻歌》的曲子中,舒曼選擇了詩人呂克特的詩獻給克拉拉:你是我的生命,我的心,你是大地,我在那兒生活,你是天空,我在那兒飛翔……
象舒曼一樣,婚後,巨大的幸福時刻包圍著克拉拉。“我完全被歡樂所占據”,那是克拉拉對自己婚姻生活最真實的表露。
然而,生活永遠不象音樂那樣美好,隨著時光的推移,災難在這個幸福家庭中悄悄地生根發芽。
3:
舒曼的父親死於精神病,這種具有遺傳性質的家族病史成了克克拉生命里永遠無法擺脫的惡魔。
1854年2月,在勃拉姆斯造訪半年後的一天,舒曼再次出現了精神虛脫的症狀,他通宵被魔鬼的聲音困擾著,無法睡眠。
一個陰雨紛紛的日子,被病痛折磨地失去了理智的舒曼競然縱身跳進了水流湍急的萊茵河,幸而被幾個好心的漁夫發現,將其送進了瘋人院。
彼時,克拉拉正在懷著舒曼的第七個孩子,而他們最大的女兒瑪麗也只14歲。望著一群不諳世事的子女,想著精神病院中瘋瘋顛顛的丈夫,克拉拉悲痛欲絕。正在外地旅行的勃拉姆斯聽到這一訊息,立即趕到舒曼的家中。
克拉拉家庭的不幸,勃拉姆斯看在眼裡,痛在心頭。他毅然放棄了成名和賺錢的機會,勇敢的承擔起了照顧克拉拉和舒曼年幼子女們的責任。
彼時的歐洲並不象今天這樣富有,許許多多的音樂家不得不是為了餬口而選擇招收學生或是登台演出,克拉拉也不例外。
接下來的兩年中,每每克拉拉外出演出時,勃拉姆斯便在家中照顧她的孩子們,並時常去瘋人院看望舒曼。
在瘋人院裡,無數地次的,勃拉姆斯看到,當他說提到克拉拉的名字,暴躁瘋顛的舒曼總會突然沉靜下來,靜靜地看著他,聽他娓娓地訴說關於克拉拉的一切,眼底的恬靜與幸福完全不象個病人。
一次,勃拉姆斯把克拉拉的照片放到舒曼的手中,這個被抑鬱症折磨的死去活來的男人哆哆嗦嗦的雙手捧著它,小心翼翼地放在唇邊親吻著,動作輕柔地就象親吻一個睡夢中的嬰兒,那種表情讓勃拉姆斯那顆痴愛著克拉拉的心抽搐不已。
沒有人知道,那個夜晚,在一池喧鬧盛開著的芳菲里,有一朵晚蓮,無奈的將所有的旖旎心事摺疊,然後,默默地,熄亡在夜色的盡頭。
4:
對克拉拉那份無法表白的愛,觸動了勃拉姆斯這位音樂天才的創作靈感,在感情與理智、感情與道德的相互撕咬下,痛苦不堪的勃拉姆斯將激情宣瀉在五線譜上,寫下了著名的《C小調鋼琴四重奏》。
在給朋友的信中,勃拉姆斯寫到:“我把這首四重奏純粹作為一件古董送給你,——它是穿藍色燕尾服和黃色背心的人的生活的最後一章的一幅插圖。請想像一個人將要開槍自殺,對於他,已沒有別的出路。”
“穿著藍色燕尾服和黃色背心的人的生活的生活的最後一章”,是指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中末尾部分,歌德對開槍自殺的維特的描寫,勃拉姆斯愛而不能的“維特式”的痛楚由此可見一斑。
無數次的,勃拉姆斯給克拉拉寫信,訴說著對克拉拉的愛與思念:即使你化塵為土,CLARA/
你死去的最愛 / 依然填滿我們之間的每一個角落 / 直到死亡再度降臨為止……
與克拉拉相識的43年裡,勃拉姆斯寫過無數封這樣的信,然而,所有的這些信,勃拉姆斯從未寄出過。
心思細敏的克拉拉當然明白這個年輕人的心事,可是,她早已將全部的身心都獻給了自己的丈夫舒曼,她珍惜勃拉姆斯的天才,原諒了勃拉姆斯充滿稚氣的愛情慾念,象個朋友與母親那樣,克拉拉用寬容與善良,引導並安撫著勃拉姆斯騷動不安的情感世界。
5:
1856年,被病痛折磨的痛苦不堪的舒曼以自殺的慘烈方式結束了自己年僅47歲的生命。舒曼的葬禮結束的第二天,勃拉姆斯悄悄的離開了這座令他一生都放心不下的城市。他知道,自己此生永遠無法代替舒曼在克拉拉心中的位置,他更不想因了自己的存在讓克拉拉陷入世俗的流言蠻語中。
舒曼的死,另克拉拉的世界頓時陷入一片灰暗之中,從此,年僅38歲的克拉拉關閉了愛情的心門,用長長的濃濃的睫,將水樣的眼眸阻隔在了紅塵之外,在孤獨中,一任瓣瓣芳華無聲地凋零,飄向流水落花。
原本, 勃拉姆斯想用離去的方式讓自己心愛的女人從此開始一份安靜的生活,然而災難並不因為勃拉姆斯的離去而放過克拉拉,她的兒女們接二連三的不幸一次次令這個堅強的女人心力憔悴:艾米爾只在這個世界上存活了16個月便夭折了;20歲的朱莉和最小的費利克斯均死於肺結核;尤金是同性戀,與母親不合;最年長的瑪莉一生鬱鬱寡歡;最讓人痛心的是路德維希,象他的父親舒曼一樣,這個年輕人也在正值壯年之際因為精神病發作被送進了瘋人院。
克拉拉的不幸,讓深愛著她的勃拉姆斯心如刀絞,他的人雖然離開了克拉拉,但他的心卻一直在她身上。一次次地,勃拉姆斯將自己創作的音樂寄給克拉拉,並悄悄地資助克拉拉的演出,他知道,唯有在音樂里,克拉拉那顆被生活戳戮的千瘡百孔的心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寧。
6:
許多時候,愛一個人,並一定要得到什麼,只要心中有愛,生命里有愛的滋潤,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人牽掛著自己亦為自己所牽掛,世界也會因此變得充實、美麗起來。
當時光的刀鋒將克拉拉年輕的容顏一片片地剝落,留在勃拉姆斯心中的那份隱忍了一生的愛情,亦漸漸地由熾熱變成了波瀾不驚的平和,年復一年地,他目睹了克拉拉的衰老,心疼不已。
1895年10月,62歲的勃拉姆斯在法蘭克福見到了已是76歲高齡的克拉拉,他極為紳士的邀請她為自己彈上一曲,克拉拉愉快地答應了。
此時的克拉拉,耳朵背了,乾枯的手指亦無法象從前那樣靈活的在琴鍵上行走,然而,當她動作僵硬的彈奏完巴赫的前奏曲和賦格曲後,勃拉姆斯依舊給了她最熱烈的掌聲。
接下來,在勃拉姆斯的請求下,克拉拉又演奏起勃拉姆斯的作品來。
勃拉姆斯靜靜地聽著。跳動的音符,沿著往事留下的線索,一路追溯向上,那些飄零歲月里遺落的青春碎片,被一雙叫做愛情的隱匿的手,點點滴滴的撿起。
勃拉姆斯深情地凝望著克拉拉,眼裡溢滿了那種可以讓人融化的溫暖。
克拉拉不說話,但她比誰都清楚,千萬個春去春來的光陰里,固執的勃拉姆斯依然走不出蕭音幽咽的過往。
一曲終了,勃拉姆斯熱情的擁抱了蒼老的克拉拉。
“克拉拉,祝你永遠健康!”
“再見,約翰內斯……”
克拉拉微笑著向勃拉姆斯道別,然後,在他轉身的瞬間,兩個人同時落下淚來。
他們很清楚,此一別,也許將成為兩個人塵世間最後的相見。
7:
1896年5月20日,一代音樂女天才克拉拉與世長辭,訊息傳來,63歲的勃拉姆斯傷心不已,他不顧好友的阻攔,拖著病痛中的身體,從瑞士隻身趕往法蘭克福。
由於過度悲傷,勃拉姆斯恍惚中竟然坐反了方向。
當他在火車上輾轉顛波,終於到達法蘭克福時,卻被告之,葬禮改在波恩舉行。
當在火車上奔波了兩天兩夜的勃拉姆斯終於趕到波恩時,因他而被推遲的克拉拉的葬禮正在等待著他。
顫顫微微地,勃拉姆斯拿出他的作品《四首嚴肅的歌》,放在克拉拉的棺木前,那是他為克拉拉77歲的生日所做的曲子,然而此刻的他卻已無力演奏它們。看著十字架後躺著的那個自己愛了一生的女人,勃拉姆斯再也無法壓抑自己的感情,他的頭無力地垂在朋友魯道夫的頸上,老淚縱橫。
8:
克拉拉的去世,沉重的打擊了勃拉姆斯。從波恩回到維也納之後,勃拉姆斯迅速的衰老,知道自己將不僅於人世的他焚燒了大量的手稿和書信。
11個月後,這位音樂天才離開了這個沒有了克拉拉的世界。
為克拉拉的生日創作的《四首嚴肅的歌》,是勃拉姆斯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成了他最後的作品,遺憾的是,克拉拉生前卻沒能聽到它們。
勃拉姆斯終生未婚,他說“我最美好的鏇律都來自克拉拉”。一句樸實的、發出自內的話,無疑是一個男人對自己心愛的女人的最真摯的讚美。
從1853年初識克拉拉,到1896年克拉拉去世,整整43年,勃拉姆斯一直將自己的感情深埋於心底,一任花開花謝,寂寥無聲。一萬五千多個日日夜夜裡,每一分鐘都如一朵開在暗夜裡的煙火,足以點燃任何一顆寂寞的心,然而,直到最後,勃拉姆斯都沒將這份愛說出口,我們不知道,是該為這份理智慶幸,還是該感嘆,這份刻骨銘心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