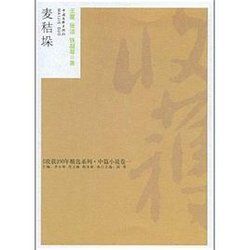內容簡介
本冊為《麥秸垛》,選取了王蒙、張潔、鐵凝等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雜色”、“同一地平線上”、“麥秸垛”等七篇作品。
作品介紹
·作者:鐵凝等
·出版社:中國文聯出版社
·頁碼:460 頁
·出版日期:2009年05月
·ISBN:7505963139/9787505963139
·條形碼:9787505963139
·包裝版本:第1版
·裝幀:平裝
·開本:16
·正文語種:中文
·叢書名:《收穫》50年精選系列
作者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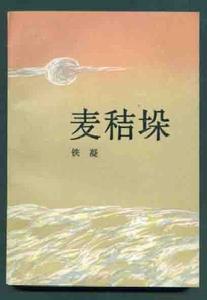 麥秸垛 鐵凝
麥秸垛 鐵凝鐵凝,著名女作家,祖籍河北趙縣,1957 年9 月生於北京,1975 年於保定高中畢業後到河北博野農村插隊,1979 年回保定,在保定地區文聯《花山》編輯部任小說編輯。自1975 年開始發表作品,至今已發表文學作品約150 餘萬字。1982 年發表短篇小說《喔,香雪》描寫一個農村少女香雪在火車站用一籃雞蛋向一個女大學生換來一隻渴望已久的鉛筆盒,表現了農村少女的純樸可親和對現代文明的嚮往,作品獲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同年,中篇小說《沒有紐扣的紅襯衫》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它真實描寫一個少女複雜矛盾的內心世界和純真美好的品格。1984 年《六月的話題》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麥秸垛》獲1986-1987 年《中篇小說選刊》優秀作品獎。1984年鐵凝調入河北省文聯任專業作家,現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早期作品描寫生活中普通的人與事,特別是細膩地描寫人物的內心,從中反映人們的理想與追求,矛盾與痛苦,語言柔婉清新。1986 年和1988 年先後發表反省古老歷史文化、關注女性生存的兩部中篇小說《麥秸垛》和《棉花垛》,標誌著鐵凝步入一個新的文學創作時期。1988 年還寫成第一部長篇小說《玫瑰門》,它一改鐵凝以往那和諧理想的詩意境界,透過幾代女人生存競爭間的較量廝殺,徹底撕開了生活中醜陋和血污的一面。
作品序言
《收穫》文學雜誌社,座落在上海市巨鹿路一個不起眼的小院裡。院門口有一間收發室,這間收發室,很可能是中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一間收發室,沒有一個收發室像它這樣深刻地介入中國文學的歷史,尤其在網路時代以前,許多對當世以及後來產生重大影響的文學作品,就是混跡於堆積如山的郵件中,從這裡輾轉到編輯部,等待編輯們的辨識。很多年中,從郵局、收發室、到編輯部、印刷廠,再回到郵局,組成了一條隱秘的循環線路,像鏈條,周而復始地轉動,使文學同時獲得了力量和速度,經過它的轉動,中國文學就不可能再停留在原處。在文學界和讀者心中,巨鹿路675號那座花木深處的西式洋樓,不僅是一家高品質的文學加工廠,更是這個時代的精神聖地。
《收穫》的歷史,早已超出它的自身,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進入作家們的回憶錄、創作談,甚至各種版本的文學史中。進入中國當代文學史可能有許多條路徑,但每一條路徑最終都會抵達這裡。它是中國文學地圖上一個最為顯著的地標,如果我們有起碼的公正,我們就不可能無視它的存在。這不僅是因為它擁有非凡的資歷——早在1957年7月,巴金和靳以就在上海創辦了這份雜誌,到1979年以前,它一直是新中國唯一的大型純文學期刊,它發表的作品,諸如《創業史》(柳青)、《茶館》 (老舍)、《山鄉巨變》(周立波)、《野火春風斗古城》(李英儒)、《上海的早晨》 (周而復)、《雜色》(王蒙)、《美食家》(陸文夫)、《煙壺》(鄧友梅)、《人生》(路遙)、《人到中年》(諶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張賢亮)、《三寸金蓮》(馮驥才)、《我愛比爾》(王安憶)、《麥秸垛》(鐵凝)、《虛構》(馬原)、《極地之側》(洪峰)、《活著》(餘華)、《妻妾成群》(蘇童)、《信使之函》(孫甘露)、 《頑主》 (王朔)、《迷舟》(格非)、《棗樹的故事》(葉兆言)、《年月日》(閻連科)、《懷念聲名狼借的日子》(池莉)、《奔跑的火光》(方方),《東藏記》(宗璞)、《務虛筆記》(史鐵生)、《秦腔》(賈平凹)、《平原》(畢飛宇)、《額爾古納河右岸》(遲子建)等,無不代表著中國文學的最高水準,更重要的,它所呈現的,不僅僅是作品,更是標準、原則、精神,它們通過那條永動機一般的隱形鏈條,得以確認、延續和發展。無論在言說空間受到貶抑,還是在物質主義甚囂塵上的年代,《收穫》始終如一地傳布著文學的真理,把《收穫》視為一面旗幟,應不為過。尤其在今天,欲望的盛行是每一個人必須面對的事實,文學家也不例外,欲望幾乎已經成為人們的唯一靈魂或靈魂的主要部件,在欲望的強大壓力下,文學開始變得手足無措、內分泌失調,唯有《收穫》的高貴、堅定和沉著沒有絲毫改變,它證明了文學在這個益發冷酷的世界上仍然可以有尊嚴地生活。這是中國文學應有的氣質,但在這個時代里,它卻成為一個奇蹟。
這使我們有必要認真打量這本雜誌的歷史。我曾有過以這本雜誌為研究對象寫一本專著的願望,試圖通過《收穫》的個案,剖析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文學史和精神史,但因時間、精力所限,始終未能如願。編選這套叢書的動議,起於2007年,《收穫》創刊50周年的時候。對那些曾經影響過我們的作品進行分梳、整理、編選,我們看到的絕不僅僅是雜誌本身,所有經歷過的歲月都會附著在紙頁上呼嘯而來,它是一部回憶之書,一部史書,它見證了文學的傳奇和我們自身的奇蹟,它同時也是一部未來之書,因為它給我們希望。這喚起了我這位出版人的職業衝動,一種無法言喻的激情,使我在2007年春天,開始主持這套叢書的編選工作。我們通讀了《收穫》50餘年的全部作品,儘可能選擇那些既影響過時代,又不受時代的局限,具有某種超越性的作品,這是我們權衡棄取的重要標準。當然,由於篇幅的限制,或者由於著作權方面的原因,有些我們很想收選的作品,最後不得不割捨,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但無論怎樣,在歷經兩年反反覆覆的出版過程之後,這套叢書終於在2009年的春天面世,為此,我要感謝《收穫》文學雜誌社所有同仁的支持與合作,當然也要感謝出版者的努力。我曾經試圖去掉“50年”這一時間界定,但最終還是放棄了這一想法,因為我已不再把它視為一個具體的數字,而是一種象徵,是對中國文學半個多世紀的艱辛而漫長的旅程作出的精確概括。
如果用物質主義者最擅長的比喻,我想,我是觸及了中國文學的銀行中一筆最珍貴的款項。我毫不懷疑,它會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救助我們。
作品文摘
犯人李銅鐘的故事 張一弓
清明時節
清明時節為什麼總要下雨呢?那無聲的、細細密密的雨絲,如同編織著銀色的網,和紛亂的思緒糾結一起,籠罩在地委書記田振山的心頭。
田振山正坐在吉普車上,去一個偏僻的山區小縣,參加一個黨支部書記的平反大會。
這位支部書記離開人世已經十九年了。十九年來,歷史給人們帶來多少意外的紛擾。開了多少嚴峻的玩笑啊!但是,田振山始終沒有忘記這個人——李銅鐘,這個出生在逃荒路上、十歲那年就去給財主放羊的小長工,這個土改時的民兵隊長、抗美援朝的志願兵,這個復員殘廢軍人、李家寨大隊的“瘸腿支書”李銅鐘。就是這樣一個李銅鐘,臨死卻變成“勾結靠山店糧站主任,煽動不明真相的民眾.搶劫國家糧食倉庫的首犯”李銅鐘了。
而現在。歷史又作出新的判決:李銅鐘無罪。儘管縣委、地委對於李銅鐘的平反有過激烈的爭論,儘管作出平反決定以後還有一些同志對此憂心忡忡,新上任的地委書記還是決定親自參加這次平反大會。為了讓活著的人們更加聰明起來,為了把人間的事情料理得更好一些,他要到那個闊別十九年的小山寨里去,到那個被野草復蓋著的墳頭上去,為一個戴著鐐銬的鬼魂去掉鐐銬了。
吉普車在山區公路上顛簸著、急駛著。田振山打開車窗,讓清涼的山風把無聲的細雨吹灑在他刻滿皺紋的臉龐上,他合上眼睛,想起了那個發生在十九年前的奇異的故事……
二 春荒
黨支部書記李銅鐘變成搶劫犯李銅鐘,是在公元一九六零年春天。
這個該詛咒的春天,是跟罕見的饑荒一起,來到李家寨的。
自從立春那天把最後一瓦盆玉米面糊攪到那口裝了五擔水的大鍋里以後,李家寨大口小口四百九十多口,已經吃了三天清水煮蘿蔔。晌午,“三堂總管”——三個小隊食掌的總保管老槓叔,蹲在米空面淨的庫房旮旯里,偷偷哭起來:“老天爺呀!噯噯噯噯……你睜睜眼吧……你不能叫俺再挎要飯籃,噯噯噯噯……”
哭,也是一種傳染病。老槓叔的哭聲從沒有關嚴的門縫裡溜出來,首先傳染給那些掂著飯罐來食堂打湯的老婆婆們,接著又傳染給那些家裡有孩子喊飢的年輕媳婦們,再往後,就變成連男人們也無法抗拒的一場瘟疫了。
“不能哭,不能哭。”沉重的假腿在雪地里“咯吱咯吱”響著,李銅鐘從大隊部跑過來,向大家講著不能哭的道理:“哭多了,眼要疼,頭要暈哩;哭多了.也要傷身體哩。我眼下再去公社問問,說不定統銷糧有訊息啦!”
哭聲平息了。大家都無言地望著年輕的支書。這個百里挑一的強
……
作者介紹
鐵凝,女,中國作家協會主席,1957年9月生於北京。 祖籍河北趙縣。父為油畫及水彩畫家,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母親是聲樂教授,畢業於天津音樂學院。鐵凝為長女。 1975年高中畢業,因酷愛文學,放棄留城、參軍,自願赴河北博野縣農村插隊。同年《會飛的鐮刀》被收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兒童文學集。該小說是鐵凝高中時的一篇作文,後被認為是其小說處女作。 1975年至1978年在農村務農4年,此間寫出《夜路》《喪事》《蕊子的隊伍》等短篇小說,發表於《上海文藝》《河北文藝》等文學期刊。 1979年調保定地區文聯《花山》編輯部任小說編輯。冬,參加全國兒童文學創作座談會,會議期間拜望茅盾、張天翼等前輩。 1980年參加河北省文學講習班。同年,短篇小說《灶火的故事》在孫犁主辦的《天津日報》“文藝增刊”發表,《小說月報》轉載,並引起爭鳴。第一本小說集《夜路》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1982年夏,參加《青年文學》編輯部在青島舉辦的筆會,會間寫出短篇小說《喔,香雪》(發表於當年第9期《青年文學》)。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3年《喔,香雪》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同年第一部中篇小說《沒有紐扣的紅襯衫》在《十月》發表。 1984年短篇小說《六月的話題》發表於《山花》,並被改編為電視短劇。同年由保定地區文聯調河北省文聯從事專業創作,並於當年召開的河北省第四次文代會上當選為河北省文聯副主席。1985年,《沒有紐扣的紅襯衫》和《六月的話題》分別獲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根據《沒有紐扣的紅襯衫》改編的電影《紅衣少女》獲本年度中國電影“金雞獎”“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年初,在中國作家協會第4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成為該協會有史以來最年輕的一位理事。5月,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美中藝術交流中心之邀,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美國,其間在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史丹福大學及國際筆會中心美國會所與美國作家、學者座談、交流中美當代文學現狀。 1986年應邀赴挪威參加第二屆國際女作家書展,在該書展專為中國作家舉辦的“中國作家報告日”做“中國女作家與當代文學”的演講。同年中篇小說《麥秸垛》在《收穫》發表,河北省文聯召開鐵凝作品研討會。 1987年應霍英東先生之邀,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香港、澳門。中篇小說《村路帶我回家》改編為同名電影由北京電影製片廠拍攝。1988年第一部長篇小說《玫瑰門》在作家出版社大型刊物《文學四季》創刊號以頭條位置發表,次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台灣版小說集《沒有紐扣的紅襯衫》由台北新地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小說集《麥秸垛》由中國文學出版社出版。西班牙文《沒有紐扣的紅襯衫》單行本在西班牙馬德里教育出版社出版。 1989年2月,《文藝報》、作家出版社、河北省文聯在北京聯合召開《玫瑰門》研討會。同年,中篇小說《棉花垛》在《人民文學》發表。 1990年至1991年,寫出《孕婦和牛》《馬路動作》《砸骨頭》《埋人》等小說,將《喔,香雪》改編成同名電影,由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拍攝,獲第41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青春片最高獎。為首批國管專家,終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兩年間積極協助當地政府為開發野三坡旅遊風景區立項和申請資金。 1992年出版兩本散文集《草戒指》(百花文藝出版社)、《女人的白夜》(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3年,發表中篇小說《對面》。獲得該年度中國作家協會頒發的“莊重文文學獎”。 1994年,長篇小說《無雨之城》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連續4個月列為上海、深圳、北京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鐵凝認為此書並非為了暢銷而寫。被《女友》雜誌評為“中國十佳作家”。 1995年春,應美國政府之邀,參加“國際訪問者計畫”訪問美國13個州,並接受俄克拉何馬州“名譽副州長”之證書。夏,應高雄文藝家協會之邀,隨內地作家代表團訪問台灣,在台北拜會林海音先生。9月,在北京參加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非政府論壇。日本東京近代文藝社出版鐵凝小說集《給我禮拜八》,譯者池澤實芳。電視劇《遭遇禮拜八》(上下集)播出。 1996年10月,河北省作家協會從河北省文聯中獨立分設,鐵凝當選為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同年年底,在中國作家協會第5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鐵凝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同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5卷本《鐵凝文集》。 1997年秋,應美國國務院邀請,隨中國國務院智慧財產權考察團訪問美國。短篇小說《安德烈的晚上》在《青年文學》發表,多家刊物轉載,獲《小說選刊》年度獎。之後據此改編的同名電影由青年電影製片廠拍攝。被河北師範大學中文系聘為客座教授。散文集《女人的白夜》獲中國首屆“魯迅文學獎”。 1998年2月,赴香港參加香港作家協會成立10周年慶祝活動。3月,應以色列希伯萊作家協會邀請,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以色列。5月,應韓國亞洲美術館邀請,陪同父親訪問韓國。在河北省第七屆文藝振興獎評選中,獲該獎項中的最高獎“關漢卿獎”,即“個人終生成就獎”。被《萌芽》雜誌社聘為“新概念作文大賽評審”。主編10人卷《女作家影記》,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9年初,中篇小說《永遠有多遠》在《十月》發表。5月,在北京參加挪威中國文學研討會,做題為“無法逃避的好運”的專題發言。9月,河北文學館及河北省作家協會新址落成。年底長篇小說《大浴女》脫稿。 2000年初,長篇小說《大浴女》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同時該作品討論會在北京召開。9月,參加由中國社科院土辦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作品討論會。 2001年春,由小說《安德烈的晚上》改編的同名電影由青年電影製片廠拍攝並在中央電視台電影頻道播出。 2001年4月,應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協會邀請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8月,擔任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評選委員會主任委員。中篇小說《永遠有多遠》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此篇同時亦獲首屆“老舍文學獎”,《十月》文學獎,《小說選刊》年度獎,《小說月報》百花獎,北京市文學創作獎等。年末,在中國作家協會第6次代表大會上,再次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2002年初,被上海大學文學院和河北大學人文學院聘為客座教授。7月,應加拿大世界華文寫作協會邀請,參加“華人文學——海外與中國第6屆研討會”。在“文學中的文明與暴力”的主題研討中,做題為“從夢想出發”的專題演講。 8月,在河北省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再次當選為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藝術隨筆集《遙遠的完美》脫稿。日本東京近代文藝社出版鐵凝小說集《紅衣少女》,譯者池澤實芳。法文版《大浴女》即由法國比基耶出版社出版。由《永遠有多遠》改編的15集同名電視連續劇在國內40餘家電視台播出。 5種小說和散文集《誰能讓我害羞》《第十二夜》《回到歡樂》等分別由新世界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河南文藝出版社等出版。 2003年,《遙遠的完美》由廣西美術出版社出版。 應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之邀,主編5卷本《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選》。 應新加坡教育部邀請,赴新加坡“寫作營”授課。 日文版小說集《麥秸垛》由東京現代文藝社出版。 2006年11月12日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七屆全委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當選中國作家協會第七屆全委會主席,成為中國作協主席,接替已故作家巴金先生。 鐵凝1975年高中畢業即到農村插隊落戶,1979年調保定文聯《花山》雜誌任小說編輯,後到河北省作家協會專事創作。鐵凝在中學時代即開始創作,1980年出版短篇小說集《夜路》,遂為文壇矚目。從1982年起,以《喔,香雪》、《六月的話題》、《沒有鈕扣的紅襯衫》等作品,連續榮獲全國優秀短篇、中篇小說獎。作品多由日常生活揭示人物的心靈世界,語言清麗,意境悠遠。從1986年發表《麥秸垛》起始,轉向對傳統文化心裡的掘示,藝術風格也走向渾厚和冷峻。進入90年代後,鐵凝以《對面》、《永遠有多遠》等中、短篇小說,多方面地素描人生,演練才情;另一方面,她連續創作出《玫瑰門》、《天雨之城》、《大浴女》等長篇力作,以對女性命運、城市人生頗具人性深度的獨特發見和精到表現,既深得評論界的高度好評,又廣受普通讀者的熱烈歡迎。 鐵凝的主要作品有《鐵凝文集》(5卷),另有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隨筆集20餘種;部分作品譯成英、德、日、俄、西等文字在國外發表。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河北作家協會主席。
創作策略
在鐵凝的整個創作過程中,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那就是她的創作與現實生活和文學-潮流始終保持著一種不即不離的態勢。對此評論界多以“不打旗號”“不入流”“拒絕集體寫作,堅持個人寫作”來描述,實際上,這是鐵凝小說創作的一個顯著特點,更是她保持個性和取得成功的一種創作策略。
眾所周知,文學與現實生活特別是與現實政治的關係問題,不僅是一個經常被談論的理論問題,而且是每個作家都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實踐問題。今天不再提文藝為政治服務,不等於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對此,老作家孫犁主張“寫作離政治遠一點”,但“不是脫離政治”,而是“政治作為一個概念的時候,你不能做藝術上的表現”,只有“等它滲入到民眾的生活,再根據這個生活寫出作品”①。孫犁的這種主張與中國古典美學和文藝理論中提出的“不即不離”美學命題是一脈相承的。“創造與欣賞的成功與否,就看能否把‘距離的矛盾’安排妥當,‘距離’太遠了,結果是不可了解;‘距離’太近了,結果又不免讓實用的動機壓倒美感。‘不即不離’是藝術的一個最好的理想”②。或許是受前輩作家孫犁的影響,抑或對過去創作經驗教訓的記取,鐵凝的創作從開始就對文學與現實生活關係表現出一種清醒而深刻的認識,她說:“文學實在是對人生和世界的一種理解和把握,就是對人類命脈的一種探索。”③ 正是基於這種對文學並不“前衛” 但相當“到位”的真知灼見,鐵凝對宇宙人生常常採取一種不即不離的態度,其創作表現出了一種博大的人文主義、人道主義的情懷。她幾乎沒有直接反映社會重大政治生活的、緊跟甚至討好時代的作品,也沒有讓作品不堪重負地承載提出或解決政治、思想、道德、倫理等諸多方面問題的使命,她的絕大多數作品都是緊貼生活、直逼心靈和貫注著時代情感、人文精神的,甚至將其滲透在作家的全部創作過程乃至生存過程之中。
此外,對於新時期出現的傷痕、反思、改革、知青、現代派、尋根、先鋒實驗、新寫實、新狀態等文學-潮流,鐵凝往往也表現出不即不離的狀態。她拒絕潮流,既不歡呼也不反對,更沒有盲目地追風趕潮,甚至捲入其中而隨波逐流,而是在派別林立的文壇保持了自己特有的一份冷靜、一份從容、一份自信。同時,鐵凝並不排斥任何新鮮有益的現代觀念和藝術技巧,而是大膽地“拿來”為自己所用。鐵凝之所以在創作上一帆風順、卓然獨立,且能保持旺盛不衰的強勁活力,從一定意義上說,來自於她的人生智慧,來自於她若即若離的創作策略。
作品分析
在《麥秸垛》中,對於農村在20世紀仍然把女人當貨物,可以隨便交換與買賣的事實也講述過。老效知道栓子喜歡他的老婆後,就向栓子提出用自己的老婆來換栓子那雙從日本兵死屍上脫下來的皮鞋。花兒是從四川的家裡逃出來被賣到這裡來的。她和因成分不好娶不到老婆的小池相處得很融洽,也被村子裡的人接受的時候,丈夫突然從四川來要人。警察和村子裡的人都認為花兒非跟他回去不可,因為花兒是逃妻。沒有人想到該問問花兒自己的意願。儘管她一百個不願跟丈夫回四川,村裡的人也都同情她,可就是沒有人站出來替她說句話。因為法律上沒有解除婚姻一天,她還是屬於她丈夫的。回到四川之後,她還能跟她丈夫離婚再回到這裡嗎?大家都知道是沒有希望的,但也只得讓她走了。鐵凝敘述故事只是娓娓道來,從不加任何評語,也聽不見她的“作者的聲音”,只有用敏銳的觸角才能體察到其中的真味。這種不做尖銳評論的寫法,也許就是郜元寶所說的柔順之美吧?
作品影響
鐵凝的中篇小說《麥秸垛》(載《收穫》1986年6期)發表後,紛紛揚揚的溢美文章便接踵而至。 這幾年來的“文化熱”,促使文學創作開始注意強化文化意識。《麥秸垛》出來後,評論界自然也以“文化”相許。說它在“對中國傳統的文化心理的開掘方面達到了一個新的層次”,①“在對民族歷史文化反思中,……具有突破意義”①,云云,不一而足。那么我們也就姑且從文化的角度談起。 “那麥秸垛從喧囂的地面勃然而起,挺挺地戳在麥場上。垛頂被黃泥壓勻,顯出柔和的弧線,似一朵碩大的蘑菇,……春天、夏天、秋天的雨和…
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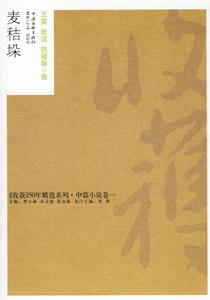 麥秸垛 鐵凝
麥秸垛 鐵凝這是一部有著豐厚象徵意味、被評論界稱之為散發著“麥秸垛意識”的中篇小說,它集中地概括了鐵凝向華北大平原縱深開掘過程中,對於人生旅程的總體把握。可以說,鐵凝早期的小說創作恰似華北大平原上初春時節剛剛返青的麥田,從凜冽的土壤中堅韌不拔地積蓄了一冬的養分,勇敢地抖擻掉嚴寒下的蒼青,以蓬勃的生命活力綠了一地,大部分作品洋溢著生命的喜悅和對真善美的渴求,以強烈的主觀抒情色彩和輕靈明麗的筆觸,渲染出一個個頗有韻味的情緒天地,進而表達出對世界複雜性的認知與批判,因而在文壇上開闢了一個獨特的新領域。
當時的鐵凝還只熱心於詩一樣的生活,尚不善於開掘真善美背後的假惡醜,在作品的藝術形式上,也多以外在的均衡為著眼點,使一些作品的人物缺少必要的厚度和立體感,隨著鐵凝對生活體察思考得更深入、更宏遠,處處深感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心態的厚重、滯緩與頑強,她還發現,勞作生息在麥田裡的人們世世代代也同時將他們的生存狀態和喜怒哀樂循環往復地沉積在土地里。秋後,高高聳起的麥秸垛依然是莊稼人的好去處,依然很“莊稼院兒”情意綿綿地生活在一起。麥秸垛里繁衍著自己,也繁衍著人的生命、人的歡樂與痛苦,繁衍著一顆顆不死的靈魂。
1986 年,鐵凝沉甸甸地捧出了那極具包容性的《麥秸垛》,作為一種象徵,“麥秸垛”成了寄寓作家人生見解,凝聚著恆定文化心理和傳統文化積澱的歷史見證。以大芝娘為代表的幾代女性,在超穩定的文化傳統的束縛下,代代相因地重複著一幕幕難以解脫的生活悲劇,尤其是本該具有現代文明意識的知識青年沈小鳳,也在那深不可測的腐土的浸漬中重蹈大芝娘的復轍,然而卻連以自己所陶醉的性愛與傳宗接代亦不可得,讀來令人酸辛而震驚。我們在以《麥秸垛》為標誌的鐵凝的小說創作中可以傾聽到,一種歷史歲月的悠悠訴說,一種被摧殘、被壓抑、被扭曲的人性的呼喚,一種靈與肉相搏鬥的呻吟、苦澀和歡愉,一種足以令人從中醒悟到的深沉的曉喻和告誡,一種演繹在褐色土地上的關於人生、關於命運、關於性愛與情愛、關於倫理道德,以至關於農民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兒的層層袒露。
至此,我們也就悟出了流蕩在鐵凝筆下的“麥秸垛意識”的真諦——它明顯地區別於側重探尋民族劣根性的作品,而是在養育我們渾茫而厚重的大地下,深深掘開五千年的文化土層,於繁衍不息的麥秸垛生存方式、生命狀態中,穿透歷史,穿透人物生命的深層結構,努力揭示出那種渾然一體的民族生力與民族惰力。它既有對愚昧麻木、逆來順受的傳統的深刻反思,對傳統文化中麻木不仁愚昧無知的批判,又有對堅毅忍耐、博大寬厚的生命偉力的弘揚,對純真之美的人性的稱頌。在生存環境的殘酷剝奪和壓迫之下,幾乎每一個靈魂都表現出強烈的生命欲望和生命的痛楚,以及與痛楚相伴隨的掙扎和對民族的生存發展所做出的犧牲與奉獻。
所以,在鐵凝所創造的“麥秸垛意識”這一新的意象境界中,給予我們的絕不僅僅是對傳統的反思針砭,更有民族意志力的溫熱與信念。大芝娘固然是令人悲哀的,但我們民族也多虧因了大芝娘們的養育才生生不息。大藝娘的命運是一個非常古老而又動人的故事模式,古老得幾乎人人都能倒背如流。
寫作意圖
鐵凝何以要寫這樣一個故事?其中有對自然母性的崇敬,也有對傳統文化的淵源流長及生命的生生不息的歌頌,更有對現實中被扭曲了的女性沉重的嘆息,因此她還寫了沈小鳳的故事。沈小鳳是念過書的知青,可是在人生的選擇上她卻步了大芝娘的後塵,她死死地愛著“膩味”她的陸野明,自願地獻身於他,並像大芝娘一樣要陸野明與她生個孩子時代變遷了,社會境遇也相異了,為何仍有如此可悲而又令人崇敬的“母愛”呢?鐵凝將沈小鳳安置在充滿田園牧歌氛圍的端村,安置在大芝娘家裡與她做伴,是不自覺地呼喚女性回歸到自然狀態中去呢,還是有意展示這種直接的傳統薰陶呢?其實即使不在端村,即使沒有大芝娘的直接薰陶,沈小鳳式的女性在中國不也遍地皆是嗎?